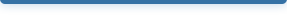程巍,1966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岳阳市,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长期致力于英美文学文化史、当代西方(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左派)文化理论和中外文学—文化关系史研究。其研究视野广阔,学术成果丰硕,代表作有《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文学的政治底稿:英美文学史论集》《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夏洛蒂·勃朗特:鸦片、“东方”与1851年伦敦博览会》《语言等级与清末民初的“汉字革命”》等。这些著作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理解和反思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9月20日,经提名、资格审查、学部评审、院外学术评鉴、公示、学部委员选举大会选举、院党组批准,我院新增9名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程巍是其中之一。近日,本报记者对程巍进行了专访,在探寻其学术成长之路的同时,带领读者一同深入了解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现状及未来发展。
把兴趣爱好变成一生志业
《中国社会科学报》:首先,恭喜您当选我院学部委员。我们想知道,您是在何种机缘下投身外国文学领域的?
程巍:我的数学能力并不出众,甚至有时会忘记自己的手机号码,同时我对科技也抱有一定的恐惧感。因此,我似乎只剩下投身文学这一条道路了。或许是因为受母亲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家里所藏的中外文学作品和文学刊物也不少。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作家和诗人的名望很高,我身边的不少小朋友都在写诗。我读的较多的是外国名著的中译本,也许由于俄苏形式主义所说的外国文学之于本国文学的“陌生化效果”,读起来觉得印象特别深刻。至于高考时选择中文还是外文,当初并没有认真思考过,但后来报考了外文。在武汉大学外文系的本科四年和北京大学硕士三年,我的阅读量很大,也非常广泛,并渐渐明确以外国文学为自己今后的学术根据地,不仅学科的延伸性较好,还能获得另一双“眼睛”。1988年我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硕士毕业,进入我院外文所外国文学理论室工作。起初,我主要研究西方当代文学文化理论方向,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后来转向英美文学文化史研究方向,再后来就转向了全球史中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文化史方向和中外文学文化关系史研究。我很幸运,一直在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兴趣没有转移,只是在不同的领域中扩展和延伸,形成了新的分支。
《中国社会科学报》:了解您的人都知道,您从大学时代就发表过不少小说作品。小说为您的科研带来了哪些灵感?
程巍:我小学就开始写诗,还获得过征文礼物。但后来发现,或者说承认自己不擅长韵律,而擅长叙事。于是,初中阶段我就转向了小说创作,后被高考前的复习中断。上大学后,时间比较自由,但读得多写得少。从研究生时期起,我在《十月》《收获》《大家》等著名文学期刊上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不过,十多年后,我回看自己的小说创作,觉得无非是在模仿,既没有属于自己的题材,也缺乏自己的写作风格,多亦无用,不如不写,由此搁笔了十几年,专心于学术研究。近两三年,我似乎突然找到了自己的题材和风格,就用零零星星的时间开始创作了。我很注重小说的叙事方式,这一点对我的学术研究颇有影响,因为我主要从事的是文学—文化史研究,而历史(包括文学—文化史)也是一种叙事;第三人称的历史叙事往往掩盖了自己的叙事者,因此也就掩盖了“谁在叙事、为何叙事、如何叙事”,但当你意识到历史是一种叙事时,就会体会到历史叙事也是一种文学“制作”,后面晃动着受制于特定语境和特定意识形态的制作人。
有人说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是难以合一的两途,其实不然。实际上,外文所就有这么一种“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传统,如冯至、李健吾、卞之琳、曹葆华、杨绛、宗璞、童道明、陈众议、陈树才、高兴、戴潍娜等学者都遵循了这一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报》:1991年您就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至今已有30余年。在您的科研生活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故事?
程巍:我进外文所工作时25岁,与外文所的学术氛围和审美趣味不谋而合。当时,外文所老一辈学者尚在,还有比他们稍晚一辈的中年学者。他们身上大多具有一种洒脱不俗的气质,大家常常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谈的主要就是文学和翻译,也喜欢品评人物。到现在,我在外文所已30多年,印象深刻的故事自然很多。例如,当时理论室的主任郭宏安先生,既是著名翻译家,又是随笔作家。有一次,我想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随他去长沙开会,坐的是60公里时速的绿皮火车,路上走了近20个小时,他一路跟我大谈“随笔之美”。到长沙后,是凌晨四点,无人接站,我和他就坐在车站正面五一路的马路边上,一边等待着天亮,一边继续谈“随笔之美”:他一直主张慎用“四字成语”,因为既然是成语,就必定带有某种程度的俗套,不能穷形尽相地描绘自己眼前的事物。对自己的写作和翻译,他以“炼字”要求自己。郭宏安先生是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一辈子在与两种文字的纠缠中发展出自己的风格。
想起自己曾经交往却已去世的外文所的老一辈和我的老师辈中的一些人,我有时有一种兰姆式的感怀。例如,童道明老师在退休后有时回到外文所,坐在椅子上,周围一圈本所的年轻人,朗读自己剧本的片段,他那种痴迷的神情,让人动容。外文所的一个可爱的风气是“没大没小”。的确,当你天天面对各国伟大的作品,当你在身边见惯了学界名流的谦逊和风趣,就会领悟到,在浩瀚的知识海洋和璀璨的人类智慧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沧海一粟。
致力于外国文学学科长远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目前外国文学学科发展现状如何?具体到外文所来说,为推进学科发展做了哪些工作?
程巍:当今,外国文学学科正在无私地为别的学科大量培养语言人才,而使自身学科日益变得荒芜。文学情怀似乎早已凋零,甚至在整个外国文学学科内皆是如此。或者说,外国文学学科目前处在一种剧烈的“格局”变化之中。一方面,学科界限被大大拓展,另一方面,文学根据地正在日蹙百里。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其实都是与“话语”的纠缠,而话语的敏感性实质就是文学的敏感性。现在我们屡屡谈到政治敏感性,但如果文学敏感性不足,又何谈政治敏感性?
外文所执着于“以语言、文学为主体,向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跨文化研究等领域拓展”,并以此为宗旨,同时结合国家的需要,对自身的研究室进行了重新调整,力争从“单一语种、单一国家、单一方法”的研究室格局走向“多语种、区域化、多学科”的新研究室格局。
经调整,外文所现有八个研究室,从名称上就可看出它们各自从事的领域:英美文学研究室更名为“英语文学研究室”,以容纳更多的英语国家和地区;俄罗斯文学研究室更名为“斯拉夫文学研究室”,以容纳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三个斯拉夫地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室更名为“外国文艺理论研究室”,因为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是可普遍运用的方法,而非一个领域,以研究领域立室才更为合理。从东方文学研究室分离出“梵文与南亚文学研究室”,中北欧—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室分为“中北欧文学研究室”与“古典学研究室”;中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暂时保持不变,待人才储备已足条件成熟,再考虑从中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分出“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研究室”。
从外文所近十几年展开的一些集体研究项目或重点学科来说,体现了一种“有组织的科研”,主要有“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主要梳理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史;“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学研究”,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文学与大国兴衰研究”,研究语言文学之于欧美各国兴衰的关系;“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从全球史视角来研究近现代中外文学及文化关系;“梵文研究”“古典学研究”以及其他国别或区域的文学研究。志同道合的学者在一个研究室长期进行相关研究,相互磨砺、相互启发、相互拓展,一定会有巨大的成效。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当前外国文学学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程巍:基于我个人的观察,一方面是外国文学学科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外国文学学科的危机。语言文学在激发一国之民的想象、磨砺其敏感性、深厚其情感和美感、为其提供人生意义、形成和维护国家统一以及身份认同、输出话语和价值、增强文化领导权等方面,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性,被认为是一国文化的精粹。此外,文学不仅提供了一套话语,还不断激发着创造性的思维。西方之崛起不仅依靠其科学技术、工商业和军事,更依靠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对共同体灵魂的建构和塑造。19世纪60年代,英国教育家和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批评英国人偏重于工商业,只追求强大,而忽视了文化,而文化才能使一国变得伟大。他提醒英国人:“假若明天英国被海水淹没,那一百年后,这两者(指工商业和文化),谁更能激发后人对英国的爱、兴趣和钦佩?”
正因为一国的语言文学如此重要,一个有志于成为全球大国或维持全球大国地位的国家,一定会一方面强化本国的语言文学,另一方面,在对外研究中,把外国语言文学作为重中之重。学习和研究外国语言文学,不仅可以丰富本国的语言文学,也是深入了解外国情形和形成“国际视野”的关键渠道。
事实证明,一国对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其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我国正处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关键过程中,对外研究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也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更有条件。中国的复兴之路急需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大力支持,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科也有待进一步发展壮大。但不无忧虑的是,走遍全国高校的外国语言文学院系,试问大学生中还有多少人在坚持文学研究并将其作为毕生事业?
开展全球史视野下的外国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有哪些研究方法或理论对外国文学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程巍:改革开放之初,一方面出于对当时文学政治化的反感,一方面缺乏对欧美文学理论的全面了解,我们引入了美国文学理论家勒雷·韦勒克的“内部研究方法”,将这种似乎“去政治化”而关注于文学内部形式本身的文学理论作为当时中国文艺学重建的基石,乃至文学学科的合法性基础。而我们所不知的是,形成于冷战之初麦卡锡主义时期的韦勒克的“内部研究方法”本身就是美国中西部重农主义、右派保守主义的一种文学意识形态。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般说法,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其特殊性正在于形式。那么,“内部研究方法”的引入并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去意识形态”,而是以一种意识形态替换了另一种意识形态。
我并不是说改革开放以来,引入的文学理论只有韦勒克的“内部研究”。相反,西方古今的文学理论,尤其是现当代的文学理论在中国遍地开花。但在学科合法性上,它们被“内部研究”贬低为“外在研究”,不是文学学科的“正宗”。但这些“边缘”理论对三四十年来一直处于霸权地位的“内部研究方法”形成了挑战,文学研究空间大大拓展,研究层面更为丰富和复杂,这也是2013年国务院学位办颁布外国文学学科新的五大方向的原因。
不过,我一直有一种观点,就是我们并没有完成“文化去殖化”的过程。而缺少这一过程,我们就受制于许多幽灵,我们的研究就有可能落入阴魂不散的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历史认知窠臼。但更多的时候,这种文化殖民化是自我施加的,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再生产——它产生了一种民族自我憎恨。文化殖民化的一个后果是瘫痪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创造力,但“文化去殖化”不是走向自我封闭,而是通过“去蔽”,通过“驱赶幽灵”,获得一种更加健康、开放、自信的态度。
新时代提出的“两个结合”对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中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研究突破当初的学科藩篱,走向彼此,催生出一种“中外文学关系史”的全球史追求。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不仅能打破此前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历史叙事模式,而且能够形成一种十分有利的“交叉的目光”。在当前的学术探索中,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审视并调整整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以确保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学术环境和研究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外国文学在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您如何看待外国文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意义?
程巍:交流的频繁程度,并不等于交流的深度。文学研究比拼的是语言和政治的双重敏感性,此外,它还广泛涉及其他学科,并且涉及想象力——文学想象力、历史想象力和社会学想象力。
不过,“外国学者”的身份也是一种优势,即具有一种不同的批评传统、意识形态和认知方式,可以独辟蹊径,对外国文学有一番本国学者未曾预料到的解读。这就像西方的女性学者、左派学者和前殖民地学者对所谓“白种—中产—男性”文学的解读,因为他们所处“位置”不同,自然别有洞天。如果一个外国学者失去自己的主体性或者说外在性,而趋同于自己研究的对象国的文学观念和方法,那么,他的角色便会退化为一种模糊的回响,仅仅重复他人的声音,失去了原创性和个人见解的独特贡献。
文学在跨文化交流中从来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跨文化交流中,文学具有一种特殊的不见行迹的渗透力量。但与一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国际地位不同,一些小国(如拉丁美洲国家)也能够成为文学大国,影响其他大国,而所谓政治、经济大国则可能是文学小国。
此外,正如俄苏形式主义者所说,“文学性”产生于对日常语言的系统偏离,而外国文学相对于本国文学来说更是一种“陌生化”,这就为外国文学的接受创造了条件。在跨文化交流中,外国文学有利于本国文学的更新和丰富;但也需要警惕,文学所携带的特定的意识形态也在跨文化交流中随着文学阅读而渗入意识乃至无意识。外国文学工作者日夕纠缠在两种语言中,受着语言的磨砺,应该更具备一种语言敏感性,而语言敏感性与政治敏感性互为表里。外国文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意义,正如辜鸿铭当初所说的“拓展”,而不是反弹回来变成一种自我封闭。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外国文学学科的未来有哪些期待?
程巍:希望它能切实地“以语言、文学为主体,向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跨文化研究等领域拓展”。实际上,外国文学研究从学科性质上说就是多学科研究,即以每一次特定的“问题”为中心,临时组合相关的学科。这意味着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多学科”“交叉学科”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联系的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我认为,或者说期待,外国文学学科将从零碎的孤立的研究渐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联系的整体,也就是说,在全球史的历史进程的全部复杂关系中研究文学。这样,才能充分体现文学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