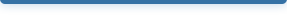20世纪以来,中国境内出土和发现了大量萨珊银币,引起中外学者广泛关注,成为相关研究的热门问题。
来自内附蕃族所纳赋税
山西省朔州市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着一枚萨珊银币,并附有说明文字:“唐代。直径2.9厘米,重3.6克。呈不规则圆形,无孔,宽平缘,两面压印有纹饰。正面是王者侧面半身像,像外是连珠圆圈。王者冕上的圆圈上有一雉堞形饰纹,圆圈外两侧及下端各饰一新月。背面正中是祭坛,其两侧各有一站立的祭司。左侧祭司外似以钵[罗]婆文铭文,可能是国王名。再外是连珠圆圈。……此枚银币应是唐时波斯国同我国通过丝绸之路往来贸易时之遗物。”根据银币国王冠式、国王形象、外缘特点及铭文,可知此钱币应为库思老一世(Khosrau I,531—579年在位)时所铸的银币。
关于我国现存的萨珊银币,孙莉等学者已进行了详细统计,大致估算为1900多枚,具体分布情况是:新疆1132枚,长安、洛阳两京附近地区560枚,甘肃23枚,青海76枚,宁夏3枚。此外,尚有河北41枚、湖北15枚、内蒙古4枚、辽宁2枚、山西50枚、广东32枚、南京1枚。近年来,在交河沟西、巴达木、木纳尔、阿斯塔那等墓地中发现银币13枚,山东东阿出土3枚。在这些统计和报道中,朔州市博物馆这枚银币并未包括在内。
库思老一世在位时间很长,达48年之久。他向东西方开疆拓土,颇有建树,其统治期堪称萨珊王朝的黄金时代。库思老一世铸币甚多,不过我国所发现的库思老一世银币并不多,此前仅陕西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河南陕县、新疆乌恰发现5枚。但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国立博物馆2015年新入藏萨珊银币200枚,其中有卑路斯一世(457—484年在位)银币16枚,卡瓦德一世(488—496、498—531年在位)银币33枚,库思老一世银币150枚。库思老一世钱币占这批钱币总数的四分之三,正体现了其铸币之多、流传之广泛。朔州市博物馆的这枚银币,为中国境内出土库思老一世银币的重要补充。
这枚萨珊银币出土于朔州市武警支队工地唐墓。究其来源,当与内附于朔州附近的铁勒等部落有关。贞观四年(630),唐平突厥颉利可汗,一些铁勒部族随突厥内附。据《册府元龟·外臣部·征讨四》记载,贞观四年三月,“思结部俟斤率众四万来降”,唐将之安置在河东代州(今山西代县)地区。内附的诸蕃族,所纳赋税与中原百姓不同,他们以“羊钱”为赋税,即如《唐六典》卷三记载:“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银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
蕃胡初附和加入唐户籍后,根据其生产生活方式,可纳银,亦可纳羊,按户等征收的银钱和羊,省称为“羊钱”。“唐仪凤三年度支奏抄”记载了银钱的征收:“其所税银钱,每年九月一日以后,十月卅日以前,各请于大州输纳。”思结部内附于代州,其他铁勒诸部内附在朔州附近,都属于“诸国蕃胡内附者”,而朔州、代州则为掌控这些蕃族的“大州”,故而收纳了内附蕃族所纳银钱和羊等。朔州市博物馆的这枚萨珊银币,可能就来自唐朔州周边内附蕃族按照户等所交纳的赋税——银钱。思结部内附在贞观初年,这枚银币也将置于代州、朔州之北的铁勒诸部交纳“羊钱”的时间提前到了贞观年间(627—649)。
与草原丝路密切相关
开元(713—741)年间,内附蕃胡纳银钱和税羊的制度在河东地区仍在实施。开元四年,漠北拔曳固斩突厥可汗默啜,铁勒的拔曳固、回纥、同罗、霫、仆固五部降唐。唐将这些部落安置在朔州之北,这些部族仍然交纳“羊钱”为税。
以银、羊为税,与唐代的赋税体系不合。唐代前期中原百姓所纳赋税,多征收粟米等谷物粮食、绢布等丝麻织品(租、调),或征各种杂物、铜钱(开元通宝),或按丁口征发徭役。以银、羊为征税物,是对内附诸国蕃胡采取的不同于华夏的特殊税制。它以内附蕃部本身的税制为模仿对象,甚至可能是沿袭内附蕃部在周边或域外的税收旧制。以羊为税,符合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税银钱则体现了草原丝绸之路上萨珊银币的贸易与流通状况,这是由草原丝绸之路的银币贸易圈决定的。
夏鼐先生指出:“萨珊银币当时在中东、近东和东欧,是和拜占庭金币一样,作为这样一种国际货币而广泛地通行使用的。”结合蒙古国发现的大量萨珊银币,可将萨珊银币的行用范围扩大到欧亚草原。隋唐时期漠北的铁勒、突厥地区为萨珊银币的行用范围,而自漠北向西,西突厥也以银币为通货。
目前,萨珊银币的传播最西至地中海沿岸,北至高加索山区。从辽东、漠北到高加索,正是突厥、铁勒诸部族及东方的奚、契丹等的活动范围。在广袤的欧亚草原上,萨珊银币都与其在中亚、西亚一样,作为通货行用。这些欧亚草原的部族,也大多以银、羊为征税对象。铁勒诸部内附后所税的银、羊,是对漠北税制、币制的延续。随着铁勒部族向唐迁徙,他们将漠北的货币形态带入太原以北,也使萨珊银币的行用范围扩展到唐农耕区的边缘,逐步进入唐朝腹地。
不论是源于漠北还是内附的铁勒部族,萨珊银币都与草原游牧民族有关。易言之,与草原丝绸之路有关。草原丝绸之路是蒙古草原地带与欧亚大陆沟通交往的交通要道,其主线为从中原地区向北,经过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北越蒙古高原,西经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至欧洲大陆北部地区。
东北草原丝绸之路是从河西,经包头、呼和浩特、大同,通过河北北部进入赤峰,到达辽宁辽阳。中国境内发现的萨珊银币,与这条草原丝绸之路路线相吻合。目前,我国山西大同、河北定县和辽宁朝阳都发现北魏时期的萨珊银币,可见萨珊银币由东北草原丝绸之路入华已有悠久的历史。《隋书·食货志》所谓的“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正是对萨珊银币行用圈的记录。
粟特人促进萨珊银币东传
北魏时期,萨珊银币通过贸易、交流、朝贡等多种途径入华,但随着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粟特商人在将银币输入至内陆欧亚草原游牧部落,并使之货币化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粟特人是中亚的商业民族。他们广泛活跃于丝绸之路上,对东西贸易贡献颇大。他们也是萨珊银币东传的主要输入者。南北朝以来,粟特商人来华者众多,携带大量萨珊银币进行经贸活动,使萨珊银币流入草原与绿洲丝绸之路。北齐、北周和隋唐时期,粟特人更多出现在突厥、铁勒等游牧部落中,著名的粟特商队首领马尼亚赫(Maniakh)即是较为突出的一个。他不但活跃在西突厥所到之处,利用突厥的军事活动开展丝绸贸易,而且还受命于西突厥可汗室点密,作为突厥使者出使拜占庭,为突厥与拜占庭建立了联系,积极扩展了丝绸贸易范围。这些粟特商人进行贸易的支付手段和价值尺度,就是自身携带的萨珊银币。伴随着粟特商人的足迹,萨珊银币行用范围扩展到草原游牧部族,进而弥漫于欧亚草原,形成了草原银币贸易圈。
从漠北扩展到唐朝腹地
铁勒部族从漠北到河东,进入太原以北,带入了游牧经济,也带来了行用的银币,将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银币贸易圈扩展到唐朝腹地。
从漠北到河东,是铁勒部族的迁徙路线,也是萨珊银币从漠北到河东的行用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更为繁盛,也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发展。朔州萨珊银币的出土,正是萨珊银币伴随铁勒迁徙之路从漠北到河东行用的证明。
大中九年(855),韦澳为唐宣宗撰《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处分语》),对朔州等地形势和民风记述为:“自代北至云、朔等州,北临绝塞之地,封略之内,杂虏所居……纵有编户,亦杂戎风。比于他邦,实为难理。”朔州地处游牧与农耕经济交界地,是唐安置漠北归附部族和阻挡漠北游牧势力南下牧马的军事重镇,故而胡汉杂居,风俗彪悍。朔州也是联系漠北草原重要通道。从朔州市唐墓中发现的萨珊银币看,草原银币贸易圈向唐腹地的扩展,并不始于开元中期,铁勒向代北的迁徙,在唐贞观四年平突厥后已经开始,河东地区的纳银钱制度已实行了近百年。因此,朔州市博物馆藏的这枚萨珊银币,正是草原丝绸之路上游牧民族对东西文化交流贡献的实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二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