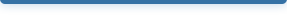中国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官制中早就有“太史令”一职。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著《史记》,提出记述历史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想把所著史书“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但后世读史者主要还是统治阶层。所以长期以来,史学的功能定位为“资治”,即对国家治理提供借鉴。为了这个目的,史家必须秉笔直书,实事实录,不说假话,由此便产生了所谓“董狐之笔”的史家道德。
“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史学的功能在近代发生了一个大提升。这还要从严复译著《天演论》,把西方一种学说介绍到了中国说起。这种学说叫做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替民族帝国主义为虎作伥的理论,其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通则,宣扬在强大的民族和国家面前,弱小一方只有“亡国灭种”的份儿。对此,读书人尤为敏感。因为当时中国已经连吃列强的败仗,特别是1894年甲午一战,还被隔壁小邻居日本欺侮得不轻,割地赔款,受尽屈辱。1897年德国强租胶州湾,这事原本不算太大,可在广州教书的康有为却立刻紧张起来,他预感列强会接二连三找上门。于是急忙到北京,冒死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变法”救国。
康有为给皇帝上的书中,讲的全是历史故事。特别是他把日本近代以来,如何从一个“蕞尔小国”通过明治维新,学习西方,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崛起成为亚洲强国的历程详加论述,这对光绪触动很大。接着康有为又给皇帝送去了一批他编写的历史书,有《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等,令光绪看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既然那么多国家的历史事实都证明“变则存,不变则亡”,还犹豫什么呢?光绪皇帝便在1898年下命令,开启变法维新。这年是农历戊戌年,史称“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大运动,这就不仅需要皇帝有觉悟,还需要百官有共识,更需要广大百姓来支持。靠什么获得这么多的共识和支持呢?还是要靠史学。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大声疾呼:“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康梁师生就这样开创了“救国史学”。
“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
随着救国史学的社会功能大提升,史书的读者对象超出了统治阶层,扩展至民众,其宣传的作用愈显突出。要想让民众都接受救国必须变法维新的道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康有为深感老百姓太保守,又迷信权威迷信经典,“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涣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为此,他专门写了两本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说千百年来被读书人奉为经典的那些东西,都是汉代刘歆伪造的,并不是真经;在《孔子改制考》中,他又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改革家孔子,说这才是真实的孔子!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我们孔圣人时代都已经有过。“读《王制》选士、造士、俊士之法,则世卿之制为孔子所削,而选举之制为孔子所创,昭昭然矣。选举者,孔子之制也。”这“两考”一出,在读书人中可谓振聋发聩。
梁启超等在帮助老师誊写这两部书稿时,心里直犯嘀咕:先生这么说能行吗?这不是“强史就我”吗?他们知道史学大家章学诚的教导:“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这就是说,史书中的义理必须以史事为根据,文则是二者的载体。根据这样原则,过去读过的“六经皆史”,而康先生突然来了一个“六经非史”,自己编出一套关于历史的新说法,这有点让他们接受不了。康有为则把梁启超等训了一通,说章学诚不是强调“史所贵者义”吗?“《春秋》所重在义,不在文与事”,孟子也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惟义所在”。我们现在都到什么时候了?要亡国灭种了!有什么“义”比救国救民更高呢?为了救国救民这个压倒一切的“义理”,“俾民信从”,以发动群众,有必要处处拘泥于“硁硁必信”的史实吗?经老师这么一说,大家都无话了。是啊,救国救民,维新变法,没有比这个更重要更崇高的事业了,为了这个政治追求,有什么方法、手段不可以拿来一用呢?
以史学来增强“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
后来,梁启超按照他老师的路数写了一篇《古议院考》的文章,引用一些历史材料,说议院在中国古已有之。这篇牵强附会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严复的来信批评。严复指出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并说孔教不可保,亦不必保,这才有利于思想进步。读了严复的信,梁启超深感“此人之学实精深,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梁启超不像康有为那么固执己见,他还是认同治史应该“力求真是真非”,从中得到“公理公例”。他批判旧史学“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力图把新史学的研究对象转向“全体国民”和“整个社会”,通过这样的史学来增强“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以达到救国的大目标。
令人遗憾的是,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只推行了三个多月就失败了。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喋血京城,康梁等一批“康党”逃亡海外。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运动中,康有为“言不必信,惟义所在”的“两考”,被那些熟读经书的清廷高官斥为别有用心的瞎胡扯,这也是光绪皇帝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让康先行离京退场的原因之一;而梁启超以社会民众为对象的新史学也难奏速效——其时平民百姓多不识字,开启“群智”还很遥远。年轻气盛的梁启超在极度失望中,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走得很近,又被老师康有为训了一通。师生二人终于在维护本党利益,坚持保皇立场上取得了一致(即主张营救身陷囹圄的光绪皇帝,继续走和平改革道路)。
为了扩大维新事业的舆论宣传,根据老师的授意,梁启超写了《戊戌政变记》一书。书中所记是一段刚刚发生过的历史,康梁都是当事人。具体史实方面,如戊戌奏折、“衣带诏”等,梁明知老师有夸大的毛病,也迁就了康有为的说辞。应该说《戊戌政变记》写得很成功。以康有为为领袖的“康党”是戊戌变法运动的核心,这一说法无可动摇地在史学界乃至民间广为流传,从而奠定了“康党”的历史地位与合法性。可是梁启超本人事后并不讳言:“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
康梁开创的救国史学,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史学影响巨大。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