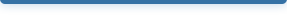朱刚是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文所”)副研究员,2007年起在我院从事民俗学及民族文学研究,研究领域包括民族文学、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个方向。
除了科研工作,朱刚在国际非遗保护领域也用力颇深。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国际培训师,他参与了多个国家的非遗培训工作,分享中国在非遗保护方面的经验;作为非遗政府间委员会审查机构前成员(中国民俗学会)代表,他深度参与了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国际评审;作为国家文化主管部门指定的专家,他也全面参与了国家层面的申遗实践如春节、二十四节气、太极拳、送王船。因其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的卓越成绩,2024年10月,他被文化和旅游部授予“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朱刚,分享他在非遗研究和保护以及推进国际合作方面的体会与思考。
学术传承奠定理论根基
《中国社会科学报》:朱刚老师好!首先,祝贺您荣获“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对于获得这个称号,您内心是什么感受?
朱刚: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这份荣誉也成为我继续深耕非遗研究、肩负科研重任的新起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这一荣誉,民文所前辈学者如朝戈金老师、巴莫曲布嫫老师多年前就获得过。我作为后辈和他们的学生,与其说是获得了一项个人荣誉,倒不如说是在前辈开拓的道路上继续奋进,凭借民文所的学术传承获得了有关部门的认可。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民文所在民俗学学科建设上是卓有成效的,一众学者获得奖掖的重要内因正在于其传承有序的学术传统。
能够获得这份荣誉,既得益于我在民文所获得的学术训练,也有赖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无与伦比的平台。非遗保护作为一种政策实践,其核心在于政府主导下各利益攸关方的协同运作,整合全社会之力共同开展非遗的系统性保护。换言之,非遗保护的关键在于制定合理、有效的保护政策。如此,我国形态多样、储量丰富的非遗资源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非遗绝不是单靠某些个体或群体就能保护好的,政府的有效主导才是非遗保护最坚实的基础。因此,我觉得这份荣誉背后,最重要的启示可能就是我们的学理研究、政策建议对政府决策形成了有效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如何走上非遗保护与民族文学研究这条学术之路的?
朱刚:与非遗、民族文学结缘可回溯到我在中国社科院读硕士的阶段。我原本不是主攻非遗的,而是专治口头诗学。民文所作为国内首家开设口头传统研究的机构,率先将诞生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口头程式理论引入中国,由此开创了口头传统研究中国学派的建设之路。口头传统这一特定领域,虽深受国外学者相关理论成果的影响,但其引入中国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西学东渐”,而更像一种理论视域上的中西相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文所在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史诗学方面的研究有着深厚积淀。我国的史诗搜集、整理工作,严格说伊始于20世纪50年代,民文所以仁钦道尔吉、郎樱、降边嘉措、杨恩洪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在口传史诗的资料建设和学术研究上作出了典范意义的成果。在他们的基础上,中生代学者代表尹虎彬、朝戈金、巴莫曲布嫫等在扎实的田野研究基础上融贯中西,为中国口头传统研究在国际民俗学理论谱系中赢得一席之地。
作为民文所的学生,我一开始立志于白族口头传统研究,并设定了从村落个案田野研究到传统歌会文化空间研究、再到西部民族地区传统歌会比较研究这一研究思路。正是在学习理论、阐释传统的过程中,我发觉单靠民俗学的一管之见,其实颇难应对歌会这一体量庞大的文化传统。口头传统研究中国学派的问题意识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学者,我们更多是处理口头诗歌的文化意义而非其创作方式的问题。此时,适逢民文所朝戈金、巴莫曲布嫫等老师正深度参与当时方兴未艾的非遗保护工作,我们在课上课下都聆听到很多基于专业又富有社会文化洞见的见解。我当时产生一种感觉:非遗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学理研究,更多与国家大政方针有关,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偏于学理的口头诗学,其理论旨归在于为人们理解中国人及中国文化提供了一种参考角度,那么偏于应用的非遗保护,其实践宗旨则在于更好地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文化保障。从上述两方面看,不论是口头传统研究,抑或中国非遗保护实践,背后当有更大的理论旨归。我们应当在思考中国文化基本问题的同时,也要考虑这些问题对于全人类的意义,并在理论上拓展那些具有普遍性的人类基本问题的反思深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学术理论建构,您有哪些思考和实践?
朱刚:民文所近几十年着力推动口头传统研究的学科建设,致力于推动口头传统研究中国学派的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口头诗学理论体系。作为本所培养的国内首批口头传统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我在口头诗学理论研究、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个案及比较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个案及理论研究等领域长期耕耘,已形成若干研究方向,并提出了民俗学中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的“交流诗学”概念。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期间,我的“交流诗学”受到时任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主任纳吉的重视,被纳入“神话与民俗2.0书系”,拟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
以“交流诗学”为指导,我开展了西部民族地区传统歌会的比较研究,力图揭示不同传统歌会文化空间的文化共性以及其中可能蕴含的有关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基本要义。同时,通过梳理教科文组织非遗保护政策演进的历史进程,我还尝试在国内非遗研究界建立一种以政策研究为导向的全新研究范式。
深刻理解文化与发展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怎样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如何看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现状?
朱刚:关于非遗的定义,相关各方主要以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为参考基准。理解非遗实际要从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出发,既要历史地看,又要比较地看。可以说,给非遗下定义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尝试。回到《公约》中的定义本身,非遗“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实际上使用了枚举法,选取了非遗若干典型的文化表现形式。其落脚点则在于,将界定非遗的权利还给拥有遗产的社区、群体和个人。转换为中文语境下的表述,就是遗产的认定要以人民为中心。
可以看到,我国的文化保护实践一直与国际社会保持一种呼应乃至同频共振。这也是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在《公约》通过之后能够取得重大成绩的原因。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双向奔赴。在政府的有效主导下,我国丰富的非遗资源得到全面识别、认定,从而进入系统的整体性保护阶段,在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维持和弘扬上作出了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口头传统与口头诗学研究对非遗保护工作有积极作用吗?
朱刚:非遗分五大领域,首要的便是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这与口头传统研究的研究对象几乎完全吻合。前面说过,口头传统研究主要侧重发掘口头性在人类构建文化系统中的功能与作用,特别要厘清以书面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对理解口头传统造成的认识论障碍。这一点与非遗保护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为更好地保护非遗,就要更深入地理解非物质表现形式与物质表现形式之间的差异。在物质遗产保护历史更深远、更受重视的前提下,如何能够回归非遗本身,跳出以物质性为中心的认知框架,可以从口头传统研究中找到理论滋养和智力支持。换言之,非遗保护的关键在于树立关于非遗重要性的观念,而树立观念的前提则在于如其所是地认识、理解非遗,祛除既有刻板偏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现代技术对传统民俗和口头传统的影响?
朱刚:民俗学中一直存在一种关于危机的叙事。民俗学向来被认为是关于传统的知识或传统之学,被视作现代的对立面。当然,这基本上是20世纪以前民俗学范式的特点。在20世纪70年代人文及社会科学普遍发生语言转向之后,民俗学实际上也完成了范式转换,对于民俗的追问变为对民众口头表达系统或艺术性交流过程的探究。这就是当代民俗学研究主要围绕人类口头艺术进行探索之问题意识的理论根源。但是,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更迭,使很多人都会有一种“越早出现越落后、越晚出现越进步”的认知倾向。然而,从口头传统、书面传统到现在的网络技术,就本质而言都可算作不同时代人类的媒介技术。与技术领域单向迭代进化即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相比,人类的三大媒介技术之间不是后代取代前代的线性发展,而是后代全面兼容前代、不同代别同时共处的局面。究其原因,人类作为社会性的生物,其存在是被文化而非技术决定的。不同的媒介技术都或有优劣且能够补益彼此,正好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活以及人类多元的文化需求。所以,现代技术无法完全取代民俗或口头传统,正如电脑、手机不能取代口头交流,而是创造条件使人类的口头交流具有了多样表现形式。但是,民俗或口头传统研究也不能摈弃技术。技术与生活的深度结合是人类发展的总体性趋势,我们既要研究技术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又要利用技术手段创新研究方法。但不论旧的或新的研究范式具有何种差异,其最终旨归仍在于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提供一种理论参考。
钟敬文先生说过,民俗学不仅是一门传统之学,更是一门现代学问,说明民俗学虽在理论视域上有其特定性,但其终极关怀却超越了时空的限定而指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规定。在当代,民俗学完成了范式转换。与此同时,在人类文明进程特别是遗产保护进程中,非遗的命名转换又为民俗学赋予了强劲的动力。这说明,当代人类的文化政策实践也在无时无刻地影响和形塑民俗学学科,民俗学理论也对遗产保护等特定领域持续发挥着指导作用。民俗学一方面与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与文化的发展有关,这注定其在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朱刚:就世界范围而言,非遗保护的最大挑战来自对文化不重视。我们常说的现代性问题,一个基本表现就是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受到挤压,现代生活方式全面取代了传统生活方式,人类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对自我的存在方式及其意义产生了更多不确定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文化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划和发展策略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003年《公约》其实都是这一核心理念的产物。因此,非遗保护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让各国政府乃至广大民众重视并深刻理解文化与发展的关系。其绝不是那种固守文化与发展绝缘的本质主义立场,而是强调在发展的维度中,让文化为人类的福祉、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助力我国非遗工作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公约》通过以来,对世界各地的非遗保护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角色和职责是什么?
朱刚:我的个人身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国际培训师,集体身份是前审查机构成员中国民俗学会辩论代表。前者主要涉及非遗的国际培训,例如曾赴平壤、伊斯兰堡、云南普洱,为朝鲜、巴基斯坦、老挝等国的政府官员讲授公约知识、申报程序、清单编制、社区参与等专题内容。后者主要涉及教科文组织的名录列入机制,即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名录、优秀实践名册、国际援助的国际评审。我作为团队代表,3年之间共参与8次审查机构评审会议,对《公约》的运行机制有相对深入的了解。
2018年,我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师资培训班,并获得该组织非遗国际培训师的认证。这为我打开了通往更广阔舞台的大门。同年,我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公室、亚太培训中心委派前往朝鲜和巴基斯坦,为当地学员讲授非遗申报程序及《公约》相关知识,同时分享了中国在非遗保护方面的丰富经验。
从2018年到2022年,我代表中国民俗学会,连续参加了五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NGO论坛,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3—17届常会。这些会议分别在毛里求斯、哥伦比亚、法国和摩洛哥等地举行,我也有幸在全球非遗保护的国际场合中与国际同行充分互动,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系统性战略布局中履职尽责。此外,作为文旅部指定专家,自2018年以来,我深度参与了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项目的履约报告撰写工作,送王船、太极拳、春节等项目列入相关名录的申报书撰写工作,以及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已列入项目的名录转移申报书撰写工作。上述申遗及履约工作方面的经验,反过来也成为我继续深入开展非遗理论研究的重要思想和实践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平衡本土文化保护与全球文化交流?
朱刚:至少在全球化这一理论预设下,各国都面临相同的挑战,即文化的标准化与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一句话概括,全球化就是将某种文化特殊性拓展为全球普遍遵循的标准。技术上的一致性可能有益于人类的生活,但文化上的标准化对人类的存续不啻灭顶之灾。保护文化并非仅保护本土文化,而是保护受到现代性影响的文化表现形式。至少从遗产保护的领域来看,遗产这一概念从原有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扩展表明,唯有各国之间携手合作才能有效保护遗产。文化之间唯有对话与交流,才能促进彼此的理解和相互欣赏,从而更加深入地认知自己所持有之文化的深刻性与重要性。非遗保护的宗旨就在于促进国际合作。遗产领域的保护实践表明,各国唯有携手,才能保护好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国际合作是推动文化在人类发展策略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关键所在。没有国际合作,文化对话、文明互鉴都将沦为空谈。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有哪些设想或计划?在中国社科院这一平台上有哪些具体的规划?
朱刚:在学术上的设想是推动非遗领域政策研究的范式转换。政策研究主要针对非遗领域,作为保护者的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作为研究者的科研人员,不能彼此隔绝、互不往来。我的想法是创造一种新的话语形式,为上述两大群体进行对话和互动提供平台,最终能使学理研究有效转换为政策制定的智力支持。民文所目前已在筹备建立院级非遗研究中心,致力在统合我院非遗研究力量的基础上成立国家级的非遗研究平台。一方面,为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提供高质量的资政建议;另一方面,为我国非遗领域的后备人才提供高质量的能力培训,以期为我国非遗保护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得益于中国社科院的殿堂级学术平台,我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很多赴外交流的机会。也是通过访学、会议、培训等交流形式,我与国外学者有了更频繁的接触、更深入的交流。我的基本感受是,国外学者对我们的了解,远远不及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但是,想要他们重视我们的研究,就需要开展积极、有效的学术对话。不能将中国材料作为验证西方理论的注脚,而要通过基于中国的理论抽绎,指出西方理论未有涉足或不能兼顾的方方面面,这样才能赢得西方学者的尊重,掌握真正的话语权。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有志于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年轻学者有哪些建议?
朱刚:要从事非遗研究,一方面需要深入了解国际非遗保护的学术史和政策演进史,另一方面也要系统学习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及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虽然非遗保护不以学理研究为其基本朝向,但唯有深刻的专业洞见方可转换为指导实践的利器。重视政策研究,要在人类共同的文化事业发展中和整体福祉的争取上,更加积极地发挥学者这一群体的特殊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