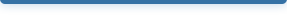1月3日清晨,郑敏先生永远告别了我们——或者用她的话说,踏上了新的未知旅途。郑先生是“九叶派”诗人当中最高寿的一叶。因其长寿,更因她一生兼顾诗歌与哲学的耕耘,在两个园地自由穿行。她思想通透,从不避讳谈论自己的死亡。她时常微笑着说,她早已收拾好了行李,随时准备启程——尽管她对人世间仍然怀着不知疲倦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郑敏先生是我国最早吸纳欧美现代派诗艺、探索现代派汉语新诗创作的先行者之一。20世纪40年代她便在诗坛成名。80年代初,郑先生与同代的老一辈诗人合作出版《九叶集》,现代主义白话诗被重新发现。这些智性趣味浓厚、以艰深晦涩的修辞及诗句为特征的诗作,与新时期呼唤新手法新气象的艺术需求一拍即合,成为诗歌爱好者们争相传诵的新经典。
不过,对于我这样一名90年代的外语系大学生,郑先生还有额外的魅力——她除了写诗,也是一位精于英美诗歌研究和文学理论探索的学者。她在外语诗歌细读上表现出的精微感受力,在诗学阐述上的强大思辨力以及明晰扼要的语言、博闻强记的学识,令我着迷、敬慕不已。1996年,我酝酿多日,终于斗胆以在读研究生身份提笔给郑先生写信,讲述研读一系列论文的心得、思考和困惑。两周后,我竟然收到了她的亲笔回信。郑先生一丝不苟回答了每个问题,细密的笔迹写满三页信纸。次年,我决定报考郑先生的博士研究生。
从广州风尘仆仆来到北京,经过两天的笔试、面试,我如愿被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录取,投身郑先生门下。那一年,她77岁,我24岁。
郑先生思维敏捷,谈话在汉语和英语之间切换自如,生动犀利,列举学术观点有条有理,引述知识典故记忆力惊人,一点不像年过七旬的老太太。我习惯了,以为这是学者的常态。后来才意识到,衰不衰老,什么年龄上衰老,固然是生物学问题、物质条件问题,也是知识储备、观念体系更新的意识问题,说白了,就是知识分子是否有意愿不断自我改造和自我革命。不管年岁多大,郑先生总是生命力饱满,思维输出惊人,这是她终身自律、学习不辍的结果。
读博期间,我每周有一个下午去她家进行学术讨论,雷打不动。工作以后,见面次数虽然锐减,郑先生与两个“旧弟子”——章燕和我仍会不定期凑成一个微型“女子沙龙”。议题是随机的,可以是任何一条阅读杂感、学术随想、时事要闻、国际事件以及由此延伸开的宏观问题——文艺、哲学、教育、民族素质、国家道路。
郑先生的言谈举止充满知识女性的优雅睿智,温柔从容。郑先生以女性气质和诗性美著称,但她从来不认为性别在文学创作或学术工作方面有什么非凡的功能,也不强调女性在两个专业领域具有什么特殊性。她甚至从来不在我们的小沙龙开启婚恋、育儿、家务、消费、养生之类通常被归为女性兴趣或特长的话题。即使跑题碰触到,她也旋即扭转回来。认识郑先生20余年,我从来不曾见过她纠结个人遭遇、感怀伤时,更不用说因为私事情绪失控或言语失态。她好像既没有为之陶醉而念念不忘的高光时刻,也没有为之不平的人生遗恨。她总是通达而冷静,兴致勃勃倾听年轻人的信息和见解,和我们一起分析问题的核心,探究未来的可能。
郑先生最该出成果的年纪正好遭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郑先生从北师大下放到山西农村支教。我曾问她是否恼恨韶华蹉跎。她非常淡然,回答说如果不是下放农村,她不会了解中国农村有多穷苦落后,她永远不能如此深刻地了解这个国家。
郑先生的家国情怀、历史使命感,远远超越了她对个人境遇的关注。郑先生在国民教育、文化建设等宏大论题上孜孜不倦地发声,也是这一精神共同体的写照。我相信郑先生的无悔是真实的。
和学长一起回忆郑先生,他最佩服郑先生不为物欲所累,轻视世俗功名,不卑不亢,永远与权力和禄蠹保持礼貌的距离;最难忘郑先生高雅迷人的生活情趣——她古典音乐修养深厚,对于水彩画和素描有独到的鉴赏力,她的家具朴素洁净,精心养育的绿植鲜花美不胜收,还有,她的茶几上永远为来客备着香甜诱人的小茶点。而我为之刻骨铭心的,则是郑先生的几次棒喝对我灵魂的雕刻,对我人生跋涉的助力。
在选择学位论文题目时,郑先生认为我理性思维方面有优势,建议我研究解构主义。我不自觉有些退缩:“解读后现代名家的批评理论,努努力我也许可以胜任,但是,怎么能对他们提出批评呢?他们是西方有名的大学问家,我仅仅是个学生,以英语为第一外语的无名小辈呀……”郑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如果你没有勇气挑战大学问家,没有做好准备与他们平等对话或辩论,你就不适合做学问,只能放弃这一行。”
学术对话和交锋的一般前提,一是双方拥有相通的知识储备,二是双方具备相同的关怀视野。郑先生却指点无名后生面对西方名家要好学也要自信,更重要的是,她指出了西学研究的一条基本原则——侧重于研究西方与我们的经验和思想有交集的话题,多关注可供我们借鉴或批判的成果,不必关心那些花哨无益的空谈。郑老师研究西方文论,没写过一篇炫耀洋货、不在乎读者是否能看懂的文章,她总是聚焦于西学与中学的对话可能,探究西学对重新认识中华语言文化的用处,这是对我影响至为深远的学术旨趣和方法。
博士三年级那年的冬天,我打算回南方过春节,向郑先生辞行。老师十分惊愕:“现在正是写论文的关键时刻,为什么中断回家?春节有什么理由必须回家?那几天和平常日子有何不同?过年过节就不读书不写作吗?”面对她咄咄逼人的目光,我想说“习俗如此”“别人都这样”,可不知为什么就是张不开口。虽然后来我还是忤逆她的想法默默回了家,但郑先生不轻易向通行的习见妥协的态度从此刻在了我心底——文学研究需要哲学推论的纯粹和追根究底。
郑先生谦虚平和,不向往聚光灯和主席台,也不害怕被冷落或被忘却。她的智慧、才华和安于边缘的一生,对于以科研为业的我具有感召力。她有着一种知识女性的自尊自律,不屑于在职业场合抛媚眼、撒娇以换取成功资源。我想做这样的人。
郑先生和我的师生情谊属于“前手机时代”。我们之间的最后一通电话,使用的仍然是8位数字座机。郑先生不喜欢交际应酬,拒绝无端浪费生命,她坚持把我们的情谊定位在单纯的学术交流上,因此,我一直尊重她的嘱咐,逢年过节不上门请安,能在电话里谈就不执于见面。
人情世故和家长里短交流不多,遗憾的是,我与郑先生往来25年,两人合影算起来统共不超过5次。2016年,忽然得知郑先生记忆力急剧衰退,我才意识到要多拍照片留住这些美好的回忆。2017年从她家告别的一刻,我第一次敢于把脸紧贴她的脸拥抱她,用肢体和皮肤的碰触表白我的情感。她变得多么瘦弱娇小啊!遗憾的是第二年我罹患眼疾,错过了会面。这两年,因新冠肺炎疫情我和郑先生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今天得知,那竟然是我和她的最后一次拥抱。
我将永远想念我的老师——郑敏先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