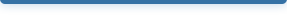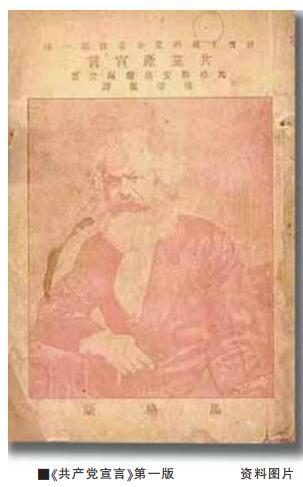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曾用名融、佛突、任重,笔名陈雪帆、晓风等。浙江义乌人。早年就读于县立绣湖书院、金华府中学堂,侧重理科。1913年考入杭州私立之江大学。1915年留学日本,先入东京物理学校,后就学于早稻田大学法科、东洋大学文科、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学士学位。1919年回国,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语文教员。1920年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这是该书最早的中译本,影响甚大,后来参与创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23年任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后兼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讲授修辞学、文学概论等课程。1927年至1931年任复旦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1929年创办中华艺术大学,任校长。1932年任上海中国著作家抗日会书记。1933年任省立安徽大学教授,讲授文艺理论等课程。次年回上海,参加发动“大众语运动”,创办《太白》半月刊。1935—1937年,任省立广西桂林师范专科学校、国立广西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科主任、教授,讲授修辞学、中国文法学等课程。1940年返回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后任新闻系主任。其间,倡导培养“有胆有识”的新闻记者,强调民主自由精神的培养,主张学以致用;主持开办通讯社、新闻馆以训练新闻实际能力。1947年当选上海市大学教授联合会主席。1949年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教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高教局局长等。1952年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1977年任复旦大学校长。1955年入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曾兼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语文学会会长、修订《辞海》总主编等。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上海政协副主席。
陈望道主要论述有《拟请议决修改初高中国文课程标准并规定大学入学试题不限文体案》《新闻馆与新闻教育改革》《两个原则——对于中国文学系改革的意见》《上海复旦大学的今昔》和《复旦十年》,著有《修辞学发凡》《美学概论》《文法简论》《因明学概略》等教科书和著作,辑有《陈望道文集》。

陈望道(1891—1977)先生的一生,是为革命艰苦奋斗的一生,也是为学术笔耕不辍的一生。在政治活动和文化建设方面,他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积极创造者和历史见证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之一,是著名社会活动家、思想家、教育家、语言学家、翻译家。他的一生,经历丰富,著作等身,贡献巨大。本文从三个侧面,还原这位革命学者独具魅力的一生。
花费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
陈望道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是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鲁迅先生在收到陈望道赠送的译本后,热情赞赏他“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曾当面盛赞:“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指的就是他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一事。为了做这“一件好事”,陈望道“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沈玄庐语)。
陈望道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县(今义乌市)分水塘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原名陈参一。在日本留学期间,恰逢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热潮传遍全球,他结识了河上肇、山川均等日本马克思主义先驱,一起开展革命宣传活动。毕业回国时,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他改名“望道”,表达自己展望新的革命道路的志向。之后不久,他在杭州推进新文化运动,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一师风潮”,从此成为名震全国文化教育界的风云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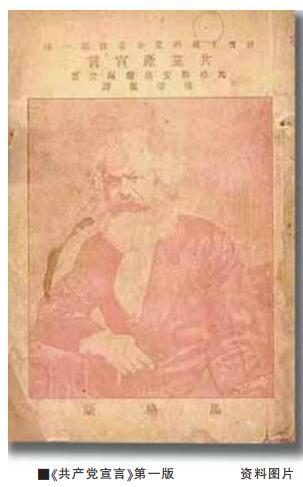
彼时,上海《星期评论》周刊的三位编辑正在为寻找《共产党宣言》的译者而犯难。他们是主编沈玄庐、戴季陶和后来参与陈望道译本校订的李汉俊。《星期评论》是当时宣传新思潮的重要阵地,他们正在积极筹划翻译《共产党宣言》,但困难重重。戴季陶彼时正对共产主义充满热情,曾尝试从日译本《共产党宣言》转译。他的日文据称“比日本人还好”,而且也擅长理论,但是他很快就知难而退。经此一译,戴季陶得出结论,认为合格的译者必须符合三个标准:熟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精通德、英、日三种外语中的一种;有相当水平的语言文学素养。
无独有偶,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罗章龙等人其时也已经着手从德文版翻译《共产党宣言》,并且提出三个标准:信、达、雅。他们同样深感《共产党宣言》理论深邃,语言精练,要达到以上三个标准殊为不易。尽管他们的译本实际上更早一点完成,但“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并没有印刷出版。翻译之难,可见一斑。甚至恩格斯自己也曾说过,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异常困难的。
正当戴季陶苦寻译者无果之时,《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编邵力子给他推荐了一个绝佳的人选,正是已在《觉悟》上刊文而崭露头角的陈望道。因“一师风潮”愤然离职的陈望道,已经认识到“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而“应该学习从制度上去看问题”,采纳“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翻译《共产党宣言》,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飞跃的契机。陈望道当然知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难度,但是他没有推辞,索性带着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和陈独秀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回到老家,在一片宁静中专心翻译。
陈望道精通日语,也熟习英文,十年的私塾教育则给他打下了绝佳的国学功底,对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向往又给了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热情和动力。1920年的早春,在自家老宅旁的柴房里,陈望道用一块铺板、两张条凳,既当书桌又当床,开始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式的翻译工作。这种开创性,一在思想,一在语言。
100年前,中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尚未形成,陈望道的工作首先是从零开始,构建一套马克思主义术语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工业革命后欧洲工人阶级的社会生活为基础,为表达以“消灭私有制”为核心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创作了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其中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怎样予以表达,才能为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劳苦大众所理解,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而且,日译本的汉字词往往不能直接照搬。为此,陈望道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两个最基本的名词“Bourgeois”和“Proletarian”,日文本译为“绅士”和“平民”,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而陈望道则译为“有产者”和“无产者”,准确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对立。
100年前,现代汉语的面貌同样也没有成熟。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新式标点还没有形成规范,作为语法基础的典范作品大多尚未面世。《共产党宣言》该采用怎样的言语说出来、说清楚,是另一项巨大的挑战。所以,陈望道的翻译,本身就是在构建新的语文体系。他此前已经对白话文的词语、文法、标点、正字法以及文章规范等有过深入思考,发表过一些论述,此刻的翻译正是付诸实践的大好机会。陈望道的译文,在风格上努力使用“引车卖浆者言”的大众语,比如“不值半文钱”“口口声声讲甚么”等;在修辞上注重韵律节奏以及语言的生动性和表现力,比如把日译本的“革命要素”换作“革命种子”;在句式上很少采用四字格,抛弃了“之乎者也”,与相距不过20年的严复和林纾的译文泾渭分明,为现代白话文奉献了一部经典。
为了跨越思想和语言两道难关,面对不到两万字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竟然耗费了两个多月。他的聚精会神、呕心沥血,集中表现在“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个小故事上。有一次,陈望道的母亲给他送来了粽子和红糖,转身出门后,担心糖不够,就问他还要不要加一些,他随口答道:“够甜,够甜了。”等到推门再进来一看,陈望道满嘴墨汁,而红糖却一点没动。原来他全神贯注于译作,竟然丝毫没有意识到粽子蘸的是墨汁。
就这样,“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换来了思想界的巨大冲击。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初版1000册供不应求。9月加印的1000册也很快售罄。其后重印、翻印数十次。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成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它面世后不到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在党外为党效劳
陈望道这一生,一颗红心,两次入党,有30多年时间是作为民主人士“在党外为党效劳”,实可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一次次重大历史事件的考验中,陈望道的共产主义初心不改、信仰不变。
在翻译完《共产党宣言》后,他于1920年4月底来到上海,投身建党大业。5月1日,他和陈独秀等人共同发起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接着,他参与筹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及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并与陈独秀一起,把《新青年》改组为党的机关刊物。1920年底,陈独秀离沪赴粤,将编务工作交给陈望道。陈独秀在致友人的信中,充分表达了对陈望道的信任:“此间事情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
陈望道主编《新青年》后,不断扩大《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使它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在胡适抛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怪论后,陈望道站在李大钊、鲁迅一边,捍卫《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办刊方向。1921年2月,法国巡捕房以《新青年》言辞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借口,将《新青年》杂志社强行封闭。陈望道不惧风险,转入地下办刊,以巨大勇气和艰辛劳动,为马克思主义宣传作出重要贡献。
然而,正当陈望道积极参与筹备党的“一大”之时,发生了一件影响他人生轨迹的“小事”。在组织活动经费的审批中,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孰料,这件小事竟刺激了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他大发雷霆,无理指责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想当“书记”。这在党组织内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陈望道曾经的学生施存统,当时尚远在日本,却因听信陈独秀的一面之词,痛心疾首地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谴责信。这件事深深伤害了陈望道的情感,他坚持要求陈独秀澄清事实、公开道歉。但以陈独秀的为人,自是不肯。这最终导致陈望道提出脱离组织,并因此错过了党的“一大”。
“一大”后陈望道担任第一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积极发展党员,培养妇女干部,组织各种宣传活动和工人运动。但是,陈独秀的说辞严重损害了陈望道的名誉,一些不明真相的年轻党员甚至指责陈望道投机革命。陈望道异常愤慨与苦闷,正式提出退党。
1923年8月,在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央委员毛泽东代表中央建议,挽留陈望道。会后,组织指定沈雁冰去劝说,陈望道则借此机会向党倾诉了衷肠:“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然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时隔多年,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陈望道深刻地自我批评,承认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性”。然而在当时,年轻的共产党和年轻的陈望道竟相互错失了30多年。
在这30多年里,陈望道用时间证明了“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他在组织上虽然不是党员,但是对党的事业始终坚贞不渝,对党交予的任务仍然不畏艰险地努力完成。正如他所说,“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他常常利用自己民主人士的身份,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1923年10月,陈望道接受组织委派,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上海大学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校刊编辑主任等职。在陈望道主持下,中国文学系的民主空气浓厚,学术研究活动也非常活跃。1929—1930年,陈望道又接受地下党组织的委派,出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为党发展左翼文艺事业,培养进步艺术人才。在他的领导下,师生们经常深入工厂、社会发动各种运动,学校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陈望道与其他进步作家陆续发起“中国著作者协会”“中国著作家抗日会”“上海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海文化界抗日联谊会”等组织,展开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的斗争。他还是上海战时语文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卢沟桥事变后,为落实周恩来的指示,陈望道发起成立“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争取到了公开的合法阵地,展开了大量的统战工作。1939年,以“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的名义,举办规模宏大的“中国语文展览会”,团结各界,对“孤岛”人民进行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1940年,陈望道来到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继续任教,后担任新闻系主任。他亲自担任学生实习的“复新通讯社”社长,保护进步学生,密切联系地下党,为党的新闻事业培养人才。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回迁上海。陈望道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大学教授联谊会”,并担任壮大后的“大学教授联合会”主席。他积极依靠地下党的领导,使该组织的各项工作得以轰轰烈烈地展开。上海解放后的1949年6月,陈望道又当选为“上海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会长。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四届代表和第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务。1952年秋,毛泽东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为团结和鼓励广大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自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做了大量工作。
1957年5月31日,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吸收陈望道入党的申请报告。毛泽东看到报告后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这是何等的信任!同年6月,陈望道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直接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陈望道终于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以革命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放在科学之外
作为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陈望道从来不标榜自己为学问而学问,而是主张“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放在科学之外”,一贯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学术研究。
少年时代的陈望道,就认识到“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要破除迷信和开发民智”,立志研究“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因为他“深切体会到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就是正确地掌握表达思想的工具,对于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是极端重要的”。
新的思想内容,需要新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因此,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白话文运动。年轻学子学习掌握白话文的需求,就是陈望道研究的动力。他回忆道:“许多学生不会写文章,问我文章怎么做,许多翻译文章翻得很生硬,于是逼着我研究修辞。”从1921年9月起,陈望道在《觉悟》上开始连载《作文法讲义》,并随后合订成册出版。这部著作全面探讨了写作技法,阐明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着眼于作文原理进行文体分类,对提升广大民众的语言文化水平非常实用。书中关于写作的本质是文字表达与思维传递相互统一的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
继作文法之后,陈望道展开了修辞学研究,目的是为了反对“当时正在社会的保守落后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见,如复古存文,机械模仿,以及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而“运用修辞理论为当时的文艺运动尽一臂之力”。他在大学开设修辞学课程,积十年之功写成《修辞学发凡》,于1932年由大江书铺出版。几十年来,该书反复重印,专家学者推崇至今。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著作,标志着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正式建立,奠定了陈望道作为该学科奠基人的学术地位。
《修辞学发凡》最根本的理念是“以语言为本位”,把修辞学纳入语言学学科框架中,确立了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扭转了“修辞”就是“修饰文辞”的文章学偏见。以此为本,陈望道提出了一些非常具有现代意义的理论观点。特别是把修辞放在语境中考察,认为“读听者”和“写说者”同样重要,以及注重消极修辞等观点,对当前的修辞学乃至语言学研究仍然具有非常直接的指导意义。
《修辞学发凡》更加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研究实践。陈望道曾说:“如果本书还有一些可取的地方,则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缘故。”首先是摆正思想内容和语言表达形式的关系问题。陈望道有意识地“用内容决定形式的观点来向形式主义进攻”,主张“研究修辞应以内容决定形式作为研究的纲领”,从内容和形式对立统一的角度,全面论述修辞现象。其次是摆正“古今中外”的关系,既做到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又反对复古主义和崇洋媚外。比如“飞白”的定名就是继承了张起南的《橐园春灯话》而没有因袭日本修辞学说法。陈望道主张要“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充分表明他已经在学术研究中成功化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方法。
陈望道也是白话文语法研究的先锋。为反对保守势力指责白话文没有“真正文法”的歪理邪说,陈望道从虚词的用法着手,例如“的”“又”“再”“和”“吗”“除非”等,逐一扎扎实实地描写它们的用法,作了精当的解说。这些研究,在用法研究以认知功能语言学为背景重新兴起的今天,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为了运用科学方法缔造新的文法体系,从1938年起,陈望道发起了中国文法革新讨论。他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善于吸收新思想,也善于博采众长,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强调以事实为准绳。这一切都决定了他在这场讨论中的中心地位。4年之后,他将讨论文章汇编为《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为汉语语法学史留下了一部经典文献。
在这场讨论中,陈望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功能论”。明确提出用功能观点来研究汉语语法,陈望道是国内第一人。他的功能主义语法观逐步发展、完善,系统体现在他晚年所著的《文法简论》中。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研究语文,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渗透到学术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从汉语的事实出发,批判地继承古代文法学术的遗产,批判地吸取外国文法学中有用的东西”。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他倡导“必须打破和改变以形态为中心的研究法,而可以采用功能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即着眼于语文的组织和词语在组织中的作用,从组织成素与成素之间的联系和关系来考察文法现象,探求文法规律”。这些观点至今仍是真知灼见。
与语言学研究相呼应,陈望道的美学研究同样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他在20世纪20年代撰写了《美学概论》《美学纲要》等专著,开创性地勾勒出了中国现代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深深地打上了苏联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烙印。他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提倡能够“与生活一致”的新文学,提出“一切艺术唯一的路”就是“出了象牙之塔,走进平民队里,制作出‘平民艺术’来”。书中毫不讳言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社会思潮对个人审美的影响,指出“分析的结果,竟如马克思们以经济的关涉于人底生活为最重要,就以它为第一个意识底成因,以为意识底成因,以为意识趣味是随经济组织底进步而进展”。
正如周恩来提出的“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有系统长时间的努力,充分掌握有关资料,从事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陈望道的科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