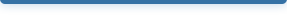“来的是谁家女子,生得满面春光,美丽非凡?这位姑娘,请你停下美丽的脚步,你可知自己犯下什么样的错误?”这句台词出自电视剧《大明宫词》中的皮影戏场景。12月20日,记者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沙垚时问到,为何他会回到乡村研究皮影戏?他回答说:“我对皮影戏有着浓厚的兴趣,至今都记得这句台词。”
除了兴趣使然,学人的选择离不开时代的召唤。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通过,并于2006年正式生效。我国第一时间以缔约国的身份加入《公约》,自此,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迎来热潮。同样是这一年,正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读大一的沙垚,在聆听了一场呼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讲座后,也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紧迫性。于是,他选择了陕西农村的皮影戏。“抢救皮影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回到农村,回到乡土文化中,成了我灵魂深处的声音。”沙垚说。
自2006年至今,沙垚在中国乡村研究这个领域深耕了18年,调研过许多村庄。其中关于皮影戏的研究,前前后后追踪了9年。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沙垚出版了《土门日记:华县皮影田野调查手记》《新农村:一部历史》《吾土吾民:农民的文化表达与主体性》《群众新闻学:理论、历史与实践》《一个人的京剧史——张正芳评传》等多部专著,发表了《可沟通关系:化解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关系的内在张力》等100余篇论文。
这些著作和论文,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不断追问中国乡村的文化基础,讨论了农民文化主体性、乡村文化内生性、乡村文化治理、乡村文化传播、乡村文化运营等议题,提出了“群众新闻路线”“可沟通关系”“乡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化转向”等原创性概念。其中,《吾土吾民:农民的文化表达与主体性》于2023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追寻:从皮影这扇窗看到广袤乡村大地
陕西省渭南市华县是沙垚做乡村调研的第一站。2007年底,沙垚与团队成员、现已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的梁君健等人再次来到这里。
与2006年暑期实践不一样的是,这次他们不只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还通过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深描”当地皮影人的情感结构和乡村的文化土壤。“其实,最初做皮影戏研究时,我只是盯着皮影戏,一直到2007年底,我去华县做第二次调研时,才关注到孕育皮影戏土壤的那个乡村。”也正是从那时起,沙垚对乡村及乡村文化有了更深的体悟。他认为,当代民间文化衰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的变迁。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应该转向历史、转向社会,去讨论艺术与社会曾经是如何进行健康而有机的互动。现在,沙垚在课堂上经常会对学生们讲,皮影戏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就像一扇窗,当我们凝视的时候,看到的不是窗,而是窗外的风景——乡村。
为了从“局外人”变成“局内人”,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当地的生活中,不仅去参加村民们举办的婚礼、葬礼、传统庙会、新型文化节活动等,还帮当地村民干农活;他们常常陪伴皮影戏老艺人流浪演出,曾在秦岭山中遭遇暴风雨,路远地滑,险些迷路;为了给一块石碑拓片,他们夜宿深山破庙,老鼠在身上跑来跑去……对于田野调查中的种种经历,沙垚至今讲述起来还是十分兴奋。田野调查结束后,当时还是本科生的沙垚出版了专著《土门日记:华县皮影田野调查手记》,那时还是硕士生的梁君健完成了影视人类学纪录片《戏末》。
2009—2011年,沙垚与团队成员赵海涛等人来到陕北,这个被沙垚习惯称作“小村”的地方。这次他将自己的调研对象直接聚焦到村庄。在这里,沙垚亲历了杨家沟和夏家峁村的建设,以平民视角,从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庙会等村落公共生活多方面展示了新农村的面貌,并提出“小村”如何选择未来的思考。
对于为什么会选择“小村”做调研,沙垚说,“‘小村’是一只麻雀,解剖它,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当时“小村”下辖的杨家沟和夏家峁村两个自然村呈现出了极其微妙的格局。其中,夏家峁村大部分村民已经完成了新村的搬迁。进入新村后可以看到两排楼板房整齐排列着,中间是一条大道,路边挂着红彤彤的灯笼。随便走进一户村民家中,冰箱、大彩电、沙发等一应俱全。而此时,杨家沟村正在经历搬迁的阵痛,一些村民不愿离开世代居住的古老窑洞。
沙垚说,这里保留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生活方式的样本:一个是满是窑洞的老村,住着不肯搬离的老人;一个是新村,崭新的楼板房,住着的大多是年轻人;还有一个是正待搬迁且矛盾重重的杨家沟。解读这些样本,可以分析出新农村建设前后的村落文化变迁。
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件事本身,沙垚表示,我坚持两点:第一,这个工程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所以不能急功近利;第二,总体来看,可以分为三步走,即完善基础设施,发展农村经济,然后是文化和社会建设。“小村”目前主要还停留在基础设施建设阶段,但隐隐地也能看出今后“小村”的发展方向,必定是以规模养殖业为主导的村落经济。
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从集体制到承包制,从新农村到城镇化,中国农村发生了或正在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农民到底在做什么、想什么?对此,人们不见得都很清楚,而这又是农村政策和文化发展的基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柳斌杰在给沙垚的书作序时写到,沙垚所做的是全景式地描写乡村,将农民创造的新的生活方式呈现出来,从政治、经济、文化、公共生活、娱乐等各个角度记录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并提出自己的思考。不仅如此,他意识到“小村”的当下状况深受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所以用讲故事的方式将几个老人口述的人生故事串联起来,以小见大,表现“小村”数十年的沧桑和变迁,一方面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纠结。中国农村正是在这样复杂的语境中,一步一步地走向未来、走向富强。
这次调研同样以“民族志”的方式进行,沙垚与团队成员在这里与村民同吃同住了100多天。但是,野外作业充满着不确定性,沙垚与团队成员一天只吃一两顿饭是常有的事;有时两个人不得不在小屋里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凑合着睡;西北缺水,他们连续15天不能洗一回脚……调研结束后,还是硕士生的沙垚写出了专著《新农村:一部历史》。
思考: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志的贯通之道
“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是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范敬宜先生对学生的教诲。“只有眼皮贴近地皮,才能看得见草根”,是一位云游诗人给沙垚的寄语。
但什么才是真实的乡村?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却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矛盾的描绘。一方面,是农村文化的复兴,农民们载歌载舞、欢声笑语,甚至还有不少浪漫化的想象,炊烟袅袅、田园牧歌;另一方面,是农村的凋敝,空心化、老龄化,以及一群不知如何安放未来的孩子。
于是,沙垚从自己的学科出发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农民有没有文化?如果有,他们如何表达自己的文化?带着这些疑问,2012年他再次回到关中农村,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与档案资料相结合的方法,累计田野工作400多天,最后搜集到一手档案3000多页,访谈500多次,音视频材料300多小时。
经过调研,沙垚发现,20世纪50年代,乡村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在实践中激烈碰撞,在复杂而艰难的互动中,锻造出新中国农民的文化主体性。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实践是农民的主要表达方式,通过细腻实践,农民在内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中穿梭,将民间性与人民性打通,创造出乡土社会的新文化传统。“只有认识到这种‘新民间性’内在的多维张力,以及汇聚在一起的坚忍维系和水滴石穿般的力量,才能真正解决当代乡村的文化困境。”沙垚说。
在学科范式上,沙垚努力探寻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志的贯通之道。传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揭示传播与政治经济宏观结构之间的权力关系;而民族志则侧重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深入具体的社会文化情景中,进行细致的文化解释。两者结合可以提供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更好地理解传播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但是,当前的民族志传播研究经常被简化为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表面形式,缺乏深层次的文化反思和理论关怀。因此,找到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志的贯通之道,有助于相关研究者深入传播学和人类学的深层脉络中,提出并解决更有意义的学术问题。
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赵月枝在看到《吾土吾民:农民的文化表达与主体性》一书后说:“这本书见证了沙垚的学术成长,他从一个完全沉浸于田野调查的学生,成长为一个努力贯通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志的青年学者。现在他在寻求政治经济学和民族志的交叉融合。他能有这样的学术自觉,我既吃惊,又欣慰。转型期中国的问题极为复杂,他走过很多村庄,在其中几个村庄驻点调研四五百天,有这样的经历,如果再加上政治经济学的素养,一定会有所建树。”
沙垚的这次调研致力于化解倾向于宏大叙事的政治经济学与倾向于微观实践的人类学民族志之间的张力,进行跨学科融合的尝试。虽然很难说这次调研的成果能够破解这一已经持续了百年的学理性范式困境,但是该成果至少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具有说服力的案例。
除此之外,这次调研成果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乡村传播研究的分析框架:“主体—时间—空间”,强调农民的文化主体性、乡村的文化内生性和历史的文化延续性。沙垚表示,该框架提出距今已近十年,但仍然具有解释力。与此同时,沙垚还在此次调研成果中较早提出农民文化主体性、乡村文化内生性等概念,并且对乡村文化内生性给出操作性定义。以民间戏曲的传承发展为例,他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路径是“实践中的人民性”等。
孕育:文化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活力
扎根乡村18载的沙垚,对乡村有着浓厚的感情。他希望为黄土高原的每一个村庄都写一部关于它的传记,希望每个村庄都可以绘就属于自己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沙垚认为,乡村既是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场域,又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重要阵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整体布局中灵魂性的存在。
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2015年起,沙垚聚焦乡村文化治理,继续做田野调查。他发现了几个有趣的现象:为什么有些村民连自己家门口的垃圾都不捡,但是红白喜事的时候,却特别有公共性?为什么有些人际矛盾,村干部解决不了,广场舞的领队一句话就解决了?这启发他思考,在乡村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实践中,包含着巨大的治理能量。如何将自上而下的行政引导与自下而上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是今天中国特色乡村治理的关键。他提出,在乡村发现文化,而不是外部性的“送文化下乡”。沙垚表示,将农村文化活动的主导权还给农民,是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也是人民史观的具体表现。这恰恰也是文化主管部门、文化产业和知识分子“有机化”的过程。
乡村振兴,文化必振兴。经过多年调研,沙垚提出,在行政和产业资源相对薄弱的乡村,文化是其重要的后发优势。对于文化赋能乡村,我们要坚持四个重要原则:一是主体性原则,以农民为主体;二是内生性原则,释放农民生活世界的正能量;三是时代性原则,体察当代农村的文化自觉;四是业余性原则,将文化实践融入日常生活。由此,动员最广泛的力量参与,激活和唤醒沉睡的文化,让文化获得与政治经济对话、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而非仅仅作为娱乐和展演,从而解决时代的迫切问题,这是我们一线乡村文化振兴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2020年以来,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在全国各地发起乡创活动。沙垚担任该院特聘研究员,参与一线实践,并对“乡创”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即在乡村进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们的乡创实践得到相关部门和业界的认可。2021年,沙垚主笔完成了相关部门委托给清华文创院的课题“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和“传承弘扬民俗节日文化研究”。2022年,文旅部在课题成果基础上联合六部委发布文件《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此外,2018年以来,他先后受邀担任北京市平谷区、江西省浮梁县、河南省光山县等十余个县(区)的乡村振兴首席顾问、首席研究员或智库导师。
2022年以来,沙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曾昕、助理研究员左灿,以及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付伟等在全国各地围绕“运营入乡”展开田野调查。当代中国已经从“乡土中国”转向了“城乡中国”,因为乡村振兴不可能仅仅依靠传统农民实现,未来乡村大概率会按照“三三制原则”,即三分之一原乡人、三分之一归乡人、三分之一入乡人形成一个新的支撑性主体。但这个新主体不会天然形成,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收入水平、价值观念等很不一样。因此,如何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进而锻造新主体;如何理解乡村的新业态和整村运营;如何看待城乡之间千万级的人口逆向流动;如何想象未来城乡融合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他们的新课题。
虽然沙垚一直以乡村传播为主要研究方向,但是他从未放弃过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追求。沙垚认为,在乡村文化宣传和新闻传播实践中,处处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这让他不得不去思考新闻与传播、历史与当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断裂和续接的问题。如果仅仅讨论乡村传播,而不去思考百年新闻史,则是一种背弃初心、隔岸观火的态度;如果仅仅讨论中国特色新闻学,而不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基层(乡村)实践相联系,则是一种刻舟求剑、掩耳盗铃的态度。
因此,沙垚通过对农村俱乐部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考察,提出了“群众新闻路线”的概念。这一路线不但是对传统新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对当前媒体环境的一种适应性创新。沙垚表示,群众新闻路线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新闻事业的遵循,又能与西方专业主义的新闻理论展开批判性对话,是一种基于实践的、自主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辩证统一的新闻生产和媒体运行模式。
“群众新闻路线”的主要特征是,沿着主体性的脉络提出,群众参与新闻生产;沿着组织性的脉络提出,新闻参与社会治理。沙垚在《群众新闻学:理论、历史与实践》中,还提出重构中国新闻学的起点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乡村实践;提出中国特色新闻学“与古为新”的新研究框架,即不再将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与历史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从历史中汲取解决当下问题和面向未来的智慧。此外,他发现“农村俱乐部”这一在中国新闻史上被忽略的研究对象,并把县级融媒体作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政治经济学实践。
无论是用民族志的方法,从社会结构与民间文化的互动视角去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尝试打通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志这两种充满隔阂与张力的研究范式,探寻乡村文化振兴的可能性路径;还是通过对农村俱乐部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考察,提出“群众新闻路线”……我们看到的是一位长期在田野调研的社科青年,在乡村研究这条学术道路上不断地探索,看到的是他想要用自己的所知所学报效祖国、服务人民。
“究竟是什么动力可以让您持续研究乡村18年?”面对记者的提问,沙垚回答说,“都是感动,对国家的、对行业的,而且所有感动最终都会落到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感动会驱动着你很努力地做事情。当然还有我的‘伯乐’——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恺先生,他对我的影响很大”。
据沙垚介绍说,史宗恺一直鼓励他跳出学科局限,将宏大的思考与微观的经验相结合。史宗恺建议沙垚用10年时间搞清楚中国农村的现状,并让他像理工科做实验一样,用一本书勾画出一个切面,进而预测50年后中国农村的样子。这种高远的学术目标和对实践的重视,促使他在乡村研究领域不断耕耘。沙垚说:“搞清楚中国农村和文化长什么样,谈何容易,太难了,我只能一直在路上。”
2015年7月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有9年,沙垚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社科青年的力量。他表示,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我们不仅要做理论阐释,更要深入实践、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群众。因为有些基层干部常常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做了很多事,探索了很多朴实、有效的经验模式,但不懂得总结提升。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结构性的“真空地带”,即对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从地方上具体的做法、实践中总结提炼中观层面的经验、模式,从而真正打通“宏观理论—中观模式—微观实践”。
对于下一阶段的重点研究方向,沙垚明确告诉记者,我现在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运营入乡”“生活入乡”应该就是未来30年中国乡村的样子,而这也将是我未来几年为之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