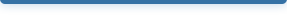什么是法?法对我们共同体生活有什么意义?人们往往把法等同于见诸法典、规章、条例的文字之法。但是,当指称“法”这个词时,心中浮现起的往往是“法”这个词的更深层次意涵:首先,法作为人类自由基石的公平正义理念,是我们每个人作为理性存在者所必须持守的根本生存规范;其次,孟德斯鸠认为“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的必然关系”,换言之,法是一种根本的世界秩序,关乎每一个存在者在世界和宇宙中的位置。德国著名法学家卡尔·拉伦茨对法之本质的探讨就告诉我们,法有其规范指向,法更是一种永恒的必然之理。
拉伦茨在《德国民法总论》第三节中讨论了“作为应当和存在的法”,这一节又相应地分为“规范秩序”和“法的存在方式”两小节,而他对“什么是法”的解说集中在“规范秩序”这一节。拉伦茨首先引用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之“法权论导论”的说法,指出“什么是法”是一个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反而不清楚的问题,就像对逻辑学家提出“什么是真理”一样,逻辑学家相信自己知道真理这个表达是什么意思,但是一旦他试图定义概念之所指时,要么同义反复,要么就只能陷入矛盾,直至最终承认:定义是不可能的。拉伦茨表明,他也不要给出一个终局性的概念规定,只是想阐明一些我们在思考法的概念时,必定会一同思考的一些“环节”。
对法律人来说,对“什么是法”最常见的回答便是,法是一种调整人们共同生活的“规范秩序”(Normenordnung),而规范秩序则意指一种普遍把握的要求或命令总体、整体,这些要求或命令向每个人提出予以遵守的要求。这种观点还意味着,人有着遵守或不遵守规范的可能,规范并不是以一种自然规律(Naturgesetz)的方式来推动人的行为,也就是说,人在面对自然规律的时候只能遵守。而规范秩序则不同,规范秩序还给了人以他种行为的可能性,为其他的动机留下了空间,在个别情况下,这些动机表明自己要更为强烈。尽管如此,法还是要求人要以合乎规范的方式行为,这种要求的法律表达就是“应当”。拉伦茨旋即指出,法的规范并不是向人发出的唯一的规范,在法规范之外,还有两种更大的规范综合体,也就是风俗和道德。风俗主要是一种社会力量,在风俗背后是一个社会群体的信念和行为方式,这个社会群体并不需要以任何一种方式被组织起来,但是在其中存在着一种“共属感”,从这种共属感中能够发展出一种共同的行为方式。风俗和法的一致之处在于,它们都满足于其命令的外在服从,但是并不要求这种服从出于正直的意向。
拉伦茨又提出了一种法和纯粹道德之间的中间状态,即主导道德,或者亨克尔(Heinrich Henkel)所说的“社会道德”,拉伦茨指出,只要社会道德有一种伦理信念现实地作为支撑,它就表现了伦理的现象形式——即便这种现象形式是削弱或粗野化的。大多数人只知道这种不完善、总是具有可疑之处的伦理形式,他们所认为的道德就是占据支配性地位的社会道德。但不能简单地把道德等同于纯粹道德或社会道德,两者都不能从伦理学领域被驱逐出去,伦理学既讨论严格伦理学的纯粹道德,也包括社会道德。德语的Sitte(风俗)和Sittlichkeit(道德/伦理)具有共同的词源,在法秩序中,我们称社会道德是“善良风俗”,它要多于单纯的风俗(习俗),但是又要少于严格的道德。在拉伦茨看来,社会道德就是黑格尔的“客观伦理”(objektive Sittlichkeit)。
法秩序在这些不同的规范领域中地位不同。在实定法的意义上理解法时,法与风俗和主导性的社会道德(它们之间在内容上已经多有触及)的共同之处在于,法是一个他律的、个体“从外部”所要面对的应当。尽管通常个体也在其自身的意识中赞同法,但是与严格伦理学的道德命令不同,个体在与法的关系中必须面对一种外在的胁迫,而不同于同样有外在胁迫的风俗和社会道德(敢于违反风俗和社会道德者可期待的只是他人的不赞同,风俗和社会道德对其并不拥有权力),法秩序则拥有直接的和规则化的强制手段。法秩序背后是组织化法共同体、国家的权力,而个人是没有能力与之对抗的。在拉伦茨看来,这种观点认为法决定性的特征就在于国家强制规范。
但是,不论是关于法律的合目的性还是把立法者的命令贯彻实施在判决中,“什么是法”这一追问都指向了正义,而康德之所以把法与真理相比较的深意就在于此。人的处境是,对于正义问题,我们并不能以一种普遍有效的方式、或一种绝对稳靠的标准来予以回答,毋宁说,在个别情况下,这种裁判似乎是正义的,而那些情况又似乎是不正义的。这也表明,尽管对人来说并没有正义的稳靠标准,但是他可以期待“法秩序”和法官的裁判,即便不是绝对正义的(这也是不可能的),但却是以正义的思想为准的,至少在原理上可以追求,在人可能的条件下实现正义的思想,避免公然“不合正义的东西”。拉伦茨由此得出结论,任何仅仅因为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地说什么是正义,就试图把正义思想、不同于实证之法的合法性之“iustum”(正义)驱逐出法和法学以及法庭之外的人,不仅仅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而且扼杀了法,扼杀了其意义以及立法者、法官及其最后的尊严与责任的活动。
紧接着,他批评了那种只把法秩序定义为规则化强制的观点,法是一种指向正义秩序理念的人类共同生活秩序,然而,现实中往往存在不正义但是有效的实定法,这类法甚至违反道德,“合乎法律的不法”(das gesetzliche Unrecht)以致非法(Nichtrecht)。但是他持有的是一种较为谦逊的正义尺度,这种正义并不以一种绝对正义的理想图景为尺度,而是说借此,特定时代和认知层次的人实现他们彼此的关系成为可能。所以,把正义的概念从法当中排除出去是毫无道理的,这样会使法成为一种纯粹的暴力秩序或者强盗联盟,是违背每个人在与法发生联系时所设想的事情的。如果在法官和立法者那里,对正义的意志、法的习惯(Rechtsethos)没有强过自私的动机,那么整个法秩序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拉伦茨进一步指出,应当(Sollen)区别于那种限制性的必须(Müssen)。如果法只是一个强制命令,那么法就是一个限制性的必须。这只是说,如果你不想遭受强制,那么你必须服从。但是实际上存在着那种不可强制的法义务,所以规范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限制性的必须。区别于必须,应当首先诉诸相对人的识见、内在的意愿、自身的法意识,它在无损于外在胁迫可能性的情况下,诉诸一种内在的胁迫,诉诸识见和善良意志。而这种诉诸只能在法规范与正义理念的意义关联中才能得到辩护。因此,以正义行事,给每个人其所应得,正义地裁判,这是一种伦理义务。当法以正义的理念为准时,那么,服从法就是道德命令,法秩序所施加的义务,用康德的话说,就是一种间接的道德义务。只有当法义务是间接的道德义务时,我们才可以称之为“义务”,因为法秩序并不能仅仅建立在外在强制的基础上,而是需要众多法共同体成员(Rechtsgenossen)行正当之事的内在意愿,因为法秩序必须在原则上把人看作是自由的。只有自由人才有义务,而且只有真正自由的人才可以认识和履行其义务。只有对那些无力实现自由的人来说,法的诉求才是一个限制性的必须。如果法义务不是真正的或间接的道德义务,那么它就是反道德的,纯粹的强制理论因此就是反自由的。由此,法与其他规范秩序的区别在于:第一,区别于风俗和社会道德,它是规则化强制的适用;第二,区别于严格伦理学(康德的道德),它的要求具有他律性质;第三,区别于所有这些规范秩序,它与正义理念有一种意义关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