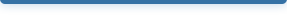◇张文博(社会学研究所)
过去半个多世纪,尤其是以30年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为标志,中国女性解放事业与推动男女平等的努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2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的主旨讲话中指出,“全球妇女命运与共。当前,实现妇女全面发展仍然面临复杂挑战”。需从营造环境、培育动能、保障治理格局和促进全球合作四个方面着力行动,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
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及中国社会转型、人口和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等时代背景下,女性发展面临一些新的系统性障碍,要求及时调整政策方向并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推动性别平等的制度努力
性别平等的早期追求主要表现为性别平权,更多关注男女两性作为社会成员资格或一国公民身份的平等权利。新中国甫一成立即颁布《婚姻法》(1950),首次在婚姻制度中提出平权要求并主张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第一部《宪法》(1954)则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传统的性别秩序在极短时间内得以改变,改写了过去“男尊女卑”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规范。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性别平权追求仍处于父权/男权语境之中。“男女都一样”在淡化性别差异的同时,表现为以男性为对照标准的“去性别化”的性别平等叙事。在此叙事之下,随着女性受教育机会和社会参与权利的提升,“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感召,让越来越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其劳动力市场参与模式也同样表现为以工业化进程中的男性标准化就业为对标,这就导致对女性在人口再生产、家庭分工等方面的生理性和社会性差异的忽视。
对性别差异的忽视在过去尚未成为一个显化的问题,因为国家在农村通过人民公社、在城市通过“单位制”等提供了托幼、食堂等公共服务,以部分替代家庭功能,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女性的家庭责任;但也掩盖了女性同时承担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双重性,遮蔽了女性的特殊需求和现实困境。这就致使这一时期的性别平权追求更多停留于“形式上的平等”,而非“实质上的平等”。换言之,因其对性别差异的忽视,平权式的性别平等追求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机会平等”的努力,无法真正回应并有效解决男女两性的起点不公和需求差异问题,从而传导为在家庭劳动和生育、抚育责任上的某些政策真空和制度缺失,并可能进一步将起点不公问题转化为结果不公问题。
这种事实上的性别不平等在市场化阶段成了更为显化的问题,引发职场歧视、工作—家庭平衡、身体权与生育权等更加复杂多元的社会议题,呼唤全社会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差异化的制度安排,推动女性从身体到劳动、从私人生活到社会价值的全面解放,以实现实质性的结果公平。
女性发展的时代新挑战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自上而下”的革命性解放,为实现女性解放和男女平权历史性地破除了系统性障碍。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的女性权益保护从理念迈向法治化。如今,我国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在教育、健康、经济参与和政治地位方面达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水平,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占比超过四成,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性超过一半,妇女事业和女性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但不容忽视的是,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女性自由全面发展也面临新的问题,既有结构性的问题,也有性别视角下的劳动分工与多重负担问题,尤其是一老一小“照顾赤字”问题的日益凸显,放大了女性发展的困境。
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之一,人口的少子老龄化与长寿化催生了照护劳动需求的高涨,一方面是劳动需求总量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密集母职、长期照护等结构性劳动需求的上升。中国社会抚养比2022年曾一度高达46.6%,给作为照护劳动主要承担者的女性,尤其是职场女性带来巨大压力,劳动重负、时间焦虑、身份认同、价值认知等诸多方面,都在持续挤压女性的身心健康和发展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体制机制研究”项目组执行了“2025年中国生活品质调查”,尝试了解当前中国民众在提升生活品质方面的需求与诉求,并甄别影响生活质量的关键领域。调查发现,在健康、家庭、收入与财富、生活环境、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10个方面中,性别反差最大的一项集中在“业余生活/自由时间”上,其中又以已育女性占据最高比例。可以看到,现代职场女性始终面临在职业身份和家庭身份的夹缝中、在双重劳动的重负下寻求工作—家庭平衡的压力,限制了“她力量”的释放和女性的自由全面发展。
社会政策迫切作出整体回应
从女性解放到女性全面自由发展,不仅关乎性别平等议题,更关乎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给予其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并不能解决差异化的起点和需求问题。女性困境的解决有赖于在正视并尊重性别差异、分工差异的基础上,进行资源匹配和可行能力的补齐;更有赖于通过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设计,重新认识以照顾为核心的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并设定其打开的新方式。而在缺乏整体性制度安排或政策工具的积极效果尚未完全显现时,“低生育陷阱”“不婚不育”等现象则凸显了当代职业女性跳出障碍的自觉选择。在女性就业改变家庭模式、少子化老龄化压缩式叠加等推动之下,女性发展日益超越性别平等范畴,要求一种朝向公平正义的社会政策作出整体回应。
事实上,国际社会已从普遍社会服务、全民基本服务和普遍照顾者模式等不同方向,作出了制度性尝试或理论性探讨。在普遍社会服务和全民基本服务方面,主要是从社会政策领域对社会保护和福利给付的理论实践出发,大体主张通过扩大公共服务实现从家庭照顾到社会照顾的转向,表现为普遍主义原则和去家庭化特征,提示了社会服务现代化体系建设的解决路径。南希·弗雷泽则结合再分配层面的经济不公和承认层面的文化不公,对“普遍养家者模式”和“照顾者平等模式”两套性别平等方案进行批判,认为前者忽视了全职女性的无酬再生产劳动和照顾工作的价值,后者则通过有酬社会工资在提升照顾工作价值的同时,进一步禁锢了女性的传统角色与性别分工,进而提出作为理想型的“普遍照顾者模式”性别平等方案。要彻底解构既往的性别规范与劳动分工,建立一个将关怀置于中心地位、朝向公平正义、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社会,并从经济、时间和服务等多重维度建立支持体系,以同时实现女性和男性的解放。就此而言,这提示了一种全新社会组织范式和实质性别平等的可能性,而从生产/再生产型社会政策到生活型社会政策的转向或可提供一些启发。
女性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须积极推动社会政策的底层逻辑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转变,在承认并尊重性别差异的基础上,以制度建设带动环境营造和能力培育,支持不同性别在家庭建设和生活领域的全面合作,共同推动实质性的性别解放和女性全面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