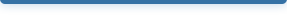西夏文是西夏景宗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在西夏王朝所统辖的今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使用约两个世纪的一种文字。尽管随着西夏国的灭亡,西夏文逐渐成为一种死文字,但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不言而喻。
为深入了解西夏文和西夏学的有关情况,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金波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和智。
解读古老文字背后的文明密码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夏文曾长期被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在19—20世纪初才被发现。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其字形结构等有哪些独特之处?
史金波:西夏是我国中古时期以党项羌为主体建立的政权,历十代帝王,后亡于蒙古。西夏灭亡后,西夏文逐渐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清嘉庆年间,学者张澍于武威游护国寺,见一砌封的石碑,拆封后看到一面文字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另一面为汉文,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天佑民安”为西夏崇宗乾顺的年号。张澍遂判定碑上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不过他的发现当时未引起学界重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法国驻北京领事馆乔治·莫里斯、费尔南·贝尔托,以及当时正在此地出差的伯希和3人趁乱捡得流失在外的西夏文《妙法莲花经》6册,上有对西夏文字的汉文对译,或为中国学者鹤龄所释读的西夏文字。19世纪末,英法学者考证北京居庸关过街塔门洞壁上六体文字石刻中的一种不明文字,前后竟花费了近20年时间,最后确认为西夏文字。
西夏文是记录党项羌语言的文字,形式和汉字相近,共有6000多字。西夏文字可分为单纯字和合体字两大类。单纯字笔画较少,从音和义的角度上不宜再分解。合体字包括合成字、互换字和对称字三类。组字时一般用一个字的一部分或全体。合成字又可分成会意合成、音意合成、音兼意合成等数种。其中会意合成是会两字之义为一义,如:“水”字的一部分加“土”字的一部分合成“泥”字。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乃至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西夏文具有很高的研究和传承价值。其价值何在?
史金波:西夏史未列入“正史”,传统史书对西夏记载十分简略,往往被称为“神秘的西夏”。近代发现了大批西夏文文献,其中记载了大量西夏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改变了西夏研究资料匮乏的局面。
创制西夏文是西夏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大量西夏文献的发现丰富了中国古代典籍。破译西夏文这种死文字、翻译西夏文典籍,进而研究西夏的社会历史文化,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填补历史文化空白的一项学术工程。
破译多种西夏文重要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说起您与西夏文,学界总会提起您和您的同事译释的《文海研究》,这本书对西夏文献的解读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但在当时学界能释读的西夏字只有2000个左右,您是怎么利用这2000多个字,最后确定了《文海研究》里5000多个西夏文的字音、字义的?
史金波:西夏文《文海研究》是一部兼有《说文解字》和《广韵》特点的重要文献。其中对每一个西夏字都有字形构造、字义和读音三项解释。认识到这部书对于释读西夏文的巨大科学价值,我从1971年便开始了艰难的翻译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才将这部共有3000多字条的文献初步译完。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白滨、黄振华二位学者陆续参加此项工作,集体进行校勘。为便于对照校勘字形和字义,我们做了全书索引,将300多页、3000多条的译稿做成数万张卡片,建成可按部首和笔画查找字的卡片库。在《文海研究》中出现的同一个西夏字的所有条目,都能集中检索出来。经过对每一字的反复比对,又新认出3000个西夏字字义。这样就识认出绝大多数西夏文常用字,加之我们又熟悉了西夏语语法,显著提高了西夏文的释读水平。1983年《文海研究》出版,后来有的专家编辑西夏文字典,便全部使用了《文海研究》中的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内容涉及西夏社会各个方面,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目前所见翻译难度最大的西夏文世俗文献。您曾组织团队用了5年左右的时间,对其进行释读。您为什么会选择翻译难度这么大的文献?您和您的团队在翻译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史金波:西夏文《天盛律令》是一部西夏政府编纂的法典,共20卷(残失1卷),有1300多页,分门别类地罗列了西夏的法律条文,全面反映了西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习俗,对研究西夏的历史和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1988年,苏联克恰诺夫教授给我寄来他出版的俄文版《天盛律令》,其中刊布了这一西夏法典的原文。我感到这部西夏法典应有从西夏文本直接翻译成汉文的译本。于是我和本院的黄振华、聂鸿音、白滨组成课题组,将此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集中力量进行翻译。
《天盛律令》是西夏原始文献,不像汉文文献翻译成西夏文的译本《论语》《孟子》等有汉文本可以参照,也不像佛经那样有汉文本可以借鉴。其中很多词语知道字面意义,但难以准确地译成汉文词语。很多语句是在反复比对、在多处出现后才能知其确切含义。如:“口缚”应译为“诉讼”,“心行”应译为“主谋”,“野入”应译为“逃跑”,“律曲”应译为“枉法”,“宽窄”应译为“背地”等。我们用了5年多的时间,将《天盛律令》译本作为《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之一出版,后又出版校改本。此书出版后,利用此书资料研究西夏社会、历史的著作和论文不断出现,推动了西夏研究。《天盛律令》译本绝大部分条目的主要内容皆比较准确,但其中也有缺漏和错误,需要不断校勘完善。现已有青年专家进行补充、校勘,并取得很好的成绩。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夏文草书是西夏研究的难点,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您初步破译了西夏文草书,并出版了《西夏社会》《西夏经济文书研究》《西夏军事文书研究》等专著,为研究西夏社会、经济、军事状况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您认为对西夏文草书的研究最难的地方是什么?此外,可否分享一下您破译西夏文草书的秘诀?
史金波:我早年曾关注、学习西夏文草书,对照汉文看西夏文草书《孝经》,能识认部分西夏文草书。然而后来集中精力破译西夏文草书,却是学术研究急需倒逼出来的事。
1997年我第3次到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整理文献时,披览俄国专家未登录的110个盒子中的文献。其中多数是佛经残卷,但我从中发现了不少反映西夏社会真实面貌的社会文书。此外,在一些西夏文佛经的封面内也发现了裱糊在其中的西夏文文书残页。这些文书多是用西夏文草书写成。因我能识别这些文书的大致属性、类别,了解到这些文书包括户籍、账籍、契约、军籍、诉讼状、告牒、书信等,深知这些文书对西夏研究的特殊价值。我便将这些文书都拣选出来,详细登录,并请摄影师一一拍照。
这些文书共得1000多件编号、1500余件。由于增加了这批超出原计划的资料,我们便将《俄藏黑水城文献》世俗部分增加3册,拟在第12、13、14册中刊布。出版这些文献,首先要给每一件文书定名,这就需要逐个了解各件文书的内容。译释清晰的西夏文楷书仍有难度,译释西夏文草书更是困难重重。这些文书还多是残页,缺头少尾,字迹不清。特别是这些文献内容直接反映西夏社会,很多词语从未见过,翻译、定名更加困难。面对上千件西夏文草书文献,整理、翻译者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我变压力为动力,花时间、拼精力去钻研。破解一件西夏文草书,要反反复复地识认、揣度,很多文书要琢磨数十遍,甚至上百遍。当年要求自己卷不离手,除每天在电脑前反复辨认、揣摩推敲外,无论在公交车上、地铁里,还是在候机室、座舱内,我都拿出西夏文文书进行识读。我对文书解读渐显成效,常常为一个难字的解破、一件新的重要文书的释读、一个重要问题的发现感到兴奋不已。
在解读西夏文草书的过程中,我不断寻求西夏文由楷书嬗变为草书的规律,识别西夏文草书的能力逐渐提高。后来我发表了《略论西夏文草书》的论文,总结了识认西夏文草书的规律。我前后用了8年的时间,得出了西夏文社会文书的定名目录,完成了这3册的出版任务。
有关西夏经济的文书约有500号,军事文书260多件。我有幸首先对这批珍贵文书进行深度研究,将其作为新的科研主攻方向。经过多年积累,我于2017年、2021年先后出版了两部有实物图片、有译文、有研究论述的《西夏经济文书研究》和《西夏军事文书研究》。这两部书不仅通过文书对西夏经济、军事进行了深入研究,也起到了学习西夏文草书的范本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文献匮乏是西夏研究的主要瓶颈,目前西夏研究在历史文献方面的情况如何?
史金波:西夏因历史文献缺乏,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往往被忽视。20世纪初,以俄国科兹洛夫为首的探险队,于中国的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了大量文献和文物,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也有相当数量的汉文及部分其他民族文字文献。他们将这批珍贵遗物席卷而走,至今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爱尔米塔什博物馆。这次发现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以后又一次重大文献发现。
1914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也从黑水城得到了不少西夏遗物,其中的西夏文文献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1917年在宁夏的灵武县也发现了不少西夏文佛经,大部分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西夏文文献和大量文物。
俄藏黑水城文献占出土西夏文文献的90%以上。20世纪60—80年代,苏联专家刊布并整理、研究了多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和汉文文献。然而与卷帙浩繁的黑水城出土文献相比,这些只是冰山一角。国内外专家都迫切期待俄藏黑水城文献尽快刊布。
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对流失到俄国的黑水城文献十分重视,希望能早日整理出版。在院领导的直接关怀下,在院科研局、外事局的指导下,我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国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达成合作,共同出版该所所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汉文和其他民族文字资料。
1993—2000年,由我带队4次组团前往俄国圣彼得堡,整理、拍摄黑水城出土文献。民族所白滨、聂鸿音,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蒋维崧(编辑)、严克勤(摄像)参加。我们采取整理拍摄一部分,及时编辑出版一部分的方法。1997年即出版了4册《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2、3、7册)。这一大型文献丛书提供了大量新的重要资料,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夏研究资料匮乏的局面。此书的出版是流失海外珍贵文献再生性回归的一个典型的成功事例。该书曾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20周年、30周年优秀成果展览。
《中国社会科学报》:《俄藏黑水城文献》共33册,出版至今已持续近30年,目前已经完成了31册。剩下的大概什么时候出版?作为主编,您如何评价这套丛书?
史金波:《俄藏黑水城文献》第32册今年出版,第33册预计明年出版。
这套丛书出版的意义在于,第一,刊布了大量新资料,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外西夏学和相关学科的繁荣发展,使西夏学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第二,它促进了中国西夏学的长足发展,从学术冷门跃升为备受瞩目的显学,促进了国内西夏研究机构的建立,使西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逐步确立。第三,此书的出版带动了藏于国内以及流失于英国、法国、日本的西夏文献的陆续整理出版。第四,为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重要的历史依据。此书中还有很多文献记录着西夏王朝与周边政权如宋、辽、金等的互动与交融,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努力推进西夏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西夏学的整体情况如何?显著特征有哪些?我院的西夏学研究有哪些特点?
史金波:近几十年来,中国的西夏学进展很快,成果很多,培养了很多后继人才,已成为国际西夏学的中心。我国学者秉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以填充西夏历史空缺为己任,在过去薄弱的基础上培根固本,潜心钻研,在多领域皆有新的突破,使西夏的历史文化的面貌逐步清晰可见。第一,重视资料建设。专家们系统梳理有关西夏的传统文献,并注重到西夏故地访查资料,还特别注重出版流失海外文献。这一阶段积累的资料红利会令学界持续受益多年。第二,注重创新研究。专家们在西夏文字语言研究、原始文献的译释,西夏社会历史的构建,乃至于西夏文草书的破译等方面,都在不断取得突破。第三,加强学术园地建设。2002年在北京图书馆出版《西夏文专号》70年之际,我们组织出版《西夏研究专号》增刊。后又出版多种西夏研究系列丛书,如《西夏研究丛书》《西夏文献研究丛书》《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等。近年来又推出《西夏学文库》,已出版著作60多种。西夏学有两种固定刊物,一是《西夏研究》,二是《西夏学》,都是西夏学研究的重要园地。第四,培养了大批人才,壮大西夏研究队伍。随着西夏研究资料的剧增,西夏学界的老、中、青专家都投入到解读、研究西夏新资料的热潮中。我们不仅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人才,还通过开设西夏文专业课培养西夏文人才。2013年我编著的《西夏文教程》出版,2020年出版了此书的英译本。不少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也参与到西夏研究队伍中来,形成了更加广泛的西夏研究队伍。第五,与藏学、敦煌学、古籍文献学等形成交叉学科。第六,与国外西夏文研究界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包括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波兰等,主要是合作出版流散于海外的西夏文献,彰显了中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力作为。
中国著名西夏学专家王静如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一生致力于西夏研究,成就非凡,贡献突出。我1962年被录取为王先生的研究生,开始从事西夏研究。同所白滨作为王先生助手,也长期做西夏研究。我们秉承西夏学研究是西夏语言、文字、历史、社会、宗教等综合性研究的理念和传统,始终将西夏历史文化作为中国历史文化一部分进行深入、填补空白的研究。后来又有聂鸿音、孙伯君、周峰、苏航等学者陆续参与研究。可以说,多年来我院的西夏研究一直处于学术前沿。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您在西夏学研究方面有何新的进展?
史金波:我现在已至杖朝之年,身体尚可,依然在西夏学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和中国民族史研究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写作10来篇论文,间或出版专著。一是做些学科发展的回顾总结工作,如前几年陆续发表了上述三个学科70年来学术发展和成就总结的论文。二是做些西夏语言、文书、文献的具体研究,发表了诸如《西夏文词语考察新得》《西夏语名词、动词兼类词初探》《俄藏5147号文书10件西夏文贷粮契译考》《〈木兰辞〉中“军书十二卷”新解——西夏军籍文书的启发》等。三是发表了有关西夏研究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论文,如《论西夏对中国的认同》《一部深度反映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奇书——〈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中的中华文明》《西夏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及其文化主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例证——中国古代合璧文字文献刍论》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史老师的学生,您是如何看待史老师的治学之道?
和智:我的老师没有爱好,只爱做学问,已经把西夏学研究与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老师具有洞察全局的眼光,善于把握学科发展的关键。他总是选择那些最重要、最需要解决的材料与问题进行研究。但凡认定需要弄清的材料与问题,他绝不轻易放弃,始终坚持不懈,默默前行,直到材料弄清、问题解决为止。西夏学代表性成果《文海研究》《天盛律令》《西夏社会》和西夏社会文书等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都体现了这一特点。陈寅恪先生认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老师使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开拓新领域,引领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西夏学研究。他不仅自己的学问做得好,也将自己的研究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们。他编纂了国内外第一本西夏文教科书《西夏文教程》,为培养学科人才、促进学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您的学生介绍,您除了读书、工作,没有其他爱好。数十年来,您为什么对西夏学研究如此钟爱?另外,您有没有想过除了工作,培养一些其他的爱好和兴趣?
史金波:我对西夏学研究有执着追求。我初学西夏文时,正是苏联和日本专家成果较多的时期。当时我便有一种责任感,要急起直追。另外西夏学研究难度大,需要做艰难的探索,具有挑战性,这样更激起我的学术兴趣。
考察文物便是我的爱好。每到一地,我尽量抽时间考察重要遗址、参观博物馆。通过考察文物我增加了很多历史知识,对历史的宏观认识也有提升。我除编纂《西夏文物》等著作外,还撰写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物综述》《宋辽夏金时期的文物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百年考古成就见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等论文。对文物的偏好也拓展了我的学术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60多年来研习西夏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您认为未来西夏学研究的方向和重点是什么?
史金波: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习了很多知识。西夏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不仅包含社会科学的多数门类,还涉及一些自然科学领域,不但要掌握好西夏文,还要具备很多学科的知识。未来,我认为中国学者在西夏学研究中应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主体责任,要厚植为国为民情怀,瞄准学术发展前沿,取得新进展。第一,继续夯实资料基础。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寻觅新的资料,译释更多重要西夏文文献;同时加大数字化力度,建设好西夏资料数据库。第二,明确主攻方向。继续向解破西夏历史文化的方向发实力、下实功、收实效;同时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考证相结合,注重总结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要贡献真知灼见。第三,攻坚克难,补足短板。西夏学研究尚存很多难点。如西夏语言还有一些现象未解破,西夏文文献中还有不少重要文献有待解破,西夏文献、文物的专题研究还需深入,西夏学的综合研究、理论探讨更需加强,要尽力打造出高质量、标志性的科研成果。第四,培养更多的高层次人才。特别是要着力培养既有学术志向,又有西夏学多领域专深业务能力,还能进行综合分析、理论探讨的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推动西夏学走向繁荣,青年学者还应从哪方面着力?
和智:从材料上看,掌握传统汉文文献,是解读西夏文文献的基础,我们需要充分了解唐代至元代的历史文献;最好还能掌握藏、羌、彝、纳西等民族语言文字和俄、日、英、法等外文。从研究方法上看,应从实证性的研究入手,从一个残片、一个地名、一个职官、一个人物的考证慢慢做起,积少成多。此外,西夏文研究者需要掌握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国瑜先生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可以作为西夏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我相信只要我辈青年学者在不断提升个人学术能力的同时精诚团结,就能更好推动西夏学研究走向繁荣。